更貼近歷史真實的“當代文學”——評洪子誠《當代文學十六講》


本世紀初,洪子誠老師在北大上《問題與方法》課,我坐在第一排。課中洪老師提到“潮汕人普通話不好”(洪老師是廣東揭陽人),本是自況。看了我一眼,洪老師又說:“陳平原例外。”滿堂鬨然。
說這件往事,是感慨於洪老師有觀察入微的能力,又有舉重若輕的精神(若筆者不是師從陳平原老師,大概也不會有這場笑談)。那年《中國當代文學史》首發,在北大中文系座談,趙園老師有“老吏斷獄”的評語,至今不能忘,亦當以此觀洪子誠老師諸書。
《當代文學十六講》是講稿,但洪老師之作,一向有講稿勝於專著的美名,如不止一人講過,中國香港版的《中國當代文學概說》勝於後來用作全國大學教材的《中國當代文學史》,蓋講稿更便於講者自由發揮,更利於單刀直入問題。簡單說,是講稿更見出講者性情,不用顧忌方方面面,更能見出講者功力。
《當代文學十六講》從1949年論及上世紀80年代,正是洪子誠老師用力最深的階段,也是他親身親歷的階段。換句話說,個人的成長與歷史的成長同步。更妙的是,洪老師一直在高校讀書、教書,是個所謂的“臭知識分子”,不曾身列工、農、兵行列,這在某種意義上避免了知識特區和信息繭房的干擾,給了他更好的觀察文學史的角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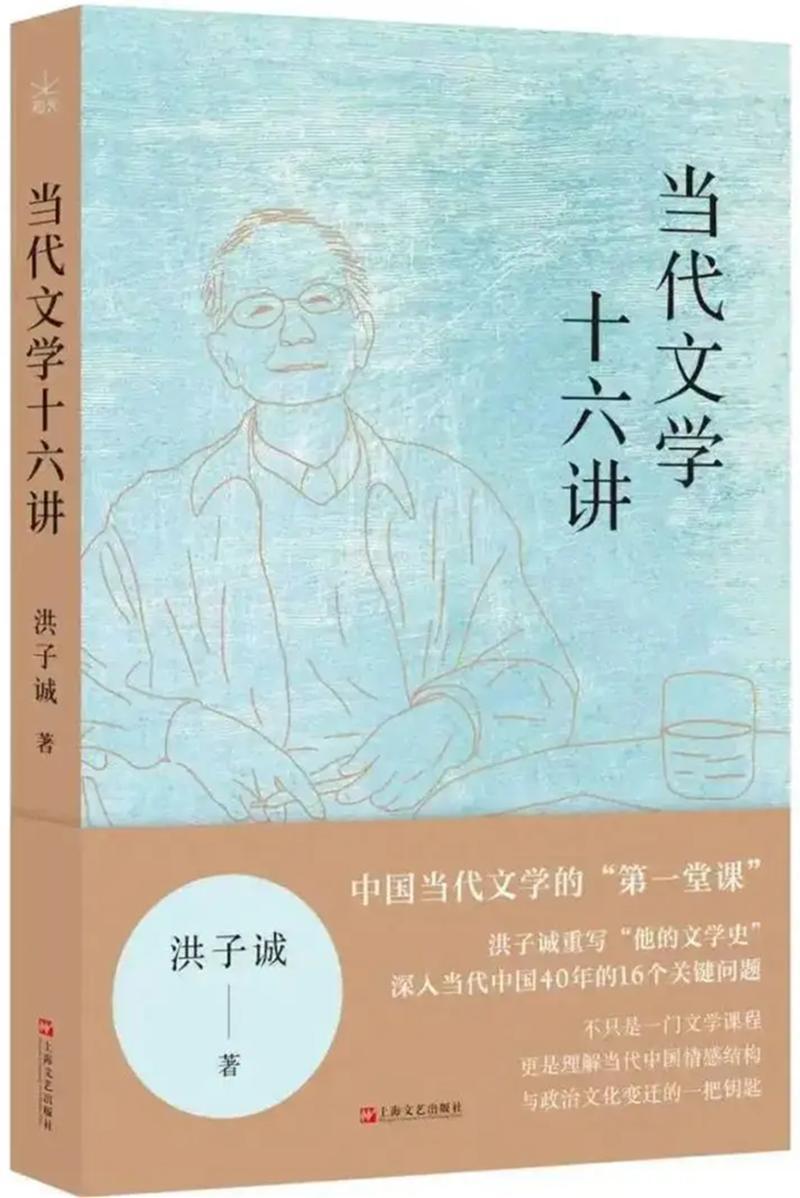
《當代文學十六講》,洪子誠 著,上海文藝出版社2025年出版
《當代文學十六講》並不是從空白開始討論“當代文學”,我想讀此書者,有三個前提是必須瞭然於心的,否則讀不通本書。這些前提如:
(一)當代文學與政治形勢密不可分,當代文學中的問題不僅僅是文學問題,還包括諸多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
(二)當代文學進程中伴隨着形形色色的政治運動;
(三)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國當代文學也不能獨立於世界文學發展。
這跟一般人想象中的“當代文學”是不一樣的,但更貼近歷史的真實。作者在第一講裏便討論《疑竇叢生的“當代文學”》,提出了“現代文學”替代“新文學”,是爲“當代文學”的生成給出空間。或者說,“當代文學”創造了“現代文學”。這個說法比較拗口,卻反映了作者的洞見:“新文學”是一種性質的界定,而“現代文學”則兼性質和時段而有之。而“當代文學”明確了現代文學的下限,也將“現代文學”的性質標示了出來。由此作者總結爲:
1949年開始的當代文學也可以看作“國家文學”,是由國家統一對文學生產全過程進行管理的文學,包括成立全國性的作家組織,國家管理文學出版、流通傳播過程,制定統一的文學方針政策,對創作的政治藝術做出鑑定、評價。(P12)
這個定義裏實際包括了筆者上述三點前提,但揭示更爲明顯、精練,也很好地闡釋了《中國當代文學史》提出的“一體化”概念。事實上,這是統攝全書的觀念,後面的闡述,要在“當代文學即國家文學”的基礎上加以理解,否則就得不出可靠的結論。
緊接着,作者爲我們繪製了一幅《當代文學的“地形圖”》,這其中既包括國統區偏“自由主義”作家的隱退,晉、陝等解放區作家羣的崛起,也包括上海作爲“文學中心”的文化衰落與北京的獨大。這一文學地理的變化,“從東南沿海向中原、西北的轉移,體現在取材、人物、風格、語言等多個方面”,“作品從比較重視學識、才情、文人傳統、日常生活、風土習俗,到更重視政治意識、社會政治運動、各個時期的政策,從更多表現市民、知識分子到更重視表現身爲‘人民’主體的工農的生活和鬥爭”。(P32)限於篇幅,作者沒有過多分析單篇作品,但是熟稔當代文學作品的人都知道,作者的概括是準確的,也是合乎邏輯的,它跟整個國家步入“新時代”有關,也奠定了當代文學的基調。
接下來,作者按照順序,拋出了當代文學中一個又一個重要問題。這些問題中,有些是當代文學界爭議已久的,如第五講《“組織部”裏的文學成規》、第六講《“人民大作家”或“鄉村治理者”》,有些是作者不止一次在論著裏講到的,如第十二講《新詩潮:尋找新的符號系統》、第十三講《拒絕的詩歌美學》,將作者擅長的當代詩歌史研究融合其中。而另一些,是此前任何一本當代文學史論著都不曾提及的,屬於近年作者的獨到見解,其特點是:將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進程放在世界文學的潮流中去考察,關注文類之間的升降及其原因,將政治動因融入文學事件之中。如第三講《“蘇聯化”與“去蘇聯化”》、第四講《中篇小說的“發明”》、第七講《歷史提的問題,回答得了麼?》、第八講《19世紀文學:“懷舊的形式”》、第九講《60年代的“戲劇中心”》,等等。有些是舊話,作者也明說吸取了其他學者的觀點,但放在全書中,卻自有一種“史”的妥帖,如第十講《當代文人的另類寫作》、第十四講《“卑微者”的小片天空》、第十五講《文學裏的城市空間》。
對於寫史最敏感的分期問題,作者用第十一講《延長線上的“新時期”》就解決了,並精闢地指出:“80年代文學,既是變革、轉折,同時也是當代50年代到70年代文學的延伸。”這一延續性,過去是認識不足的,現在提出來,是因爲“一、當代文學基本制度、觀念、藝術方法並未發生根本性改變,而是在有所調整的基礎上的延續;二、在50年代到70年代發生衝突的各種文學主張、創作傾向,到了80年代地位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某些曾被壓制、批判的論題被重新提出和肯定,如‘寫真實’‘干預生活’,如對‘現代派文學’的看法”(P180)。作者認爲,這樣做,並不是要否定80年代的重大文學變革,而且要注意“新時期”與此前文學的對話關係。不同的歷史時期,強調“變”或“不變”,因應的是不同的史述主流和歷史認知——曾有研究生告訴我,他們最難理解的不是“十七年文學”,而是八九十年代文學,這實際上就是對當代文學的本質和對話關係認識不清。新世紀以來,筆者提出的“重新發明文學”也可能看作一種“斷裂”的宣言。對於文學發展來說,宣言“斷裂”或許是必要的,但對於文學史而言,強調“連續”才能看清歷史的傳承與弔詭,理解其中的邏輯。
從體量來說,《當代文學十六講》是一本小書,也不承擔分析作品、解讀作家生平等耗費大量篇幅的任務。但是從提出問題的深度與廣度而言,這又是一本大書。作者秉持一貫的態度,知人論世往往不下斷語,而是以疑問句出之,留下後面無比廣闊的空間。讀完此書,對於“什麼是當代文學”當有一個充分的認知,這種結構性的認知纔是引導我們讀史求智的有用津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