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韓愈、歐陽修和蘇軾四大家的“道”



韓柳歐蘇一脈相承的“道”是什麼?他們又如何影響了理性精神與抒情傳統的分野?
《文以載道:唐宋四大家的道論與文學》以道學爲核心,梳理了從柳宗元、韓愈、歐陽修至蘇軾的道學傳承和文學創作,刻畫了他們作爲文學家、哲學家、政治家的立體面相,由此解讀唐宋兩代的文學復古運動。作者圍繞“文以載道”這一命題,辨析時代變革中的古文、駢文、詩、詞各文體的發展,折射出唐宋道學的發展線索。全書以史實爲依託,藉助哲學、政治史、思想史的視角,見證儒家道學如何復興,又如何重塑士大夫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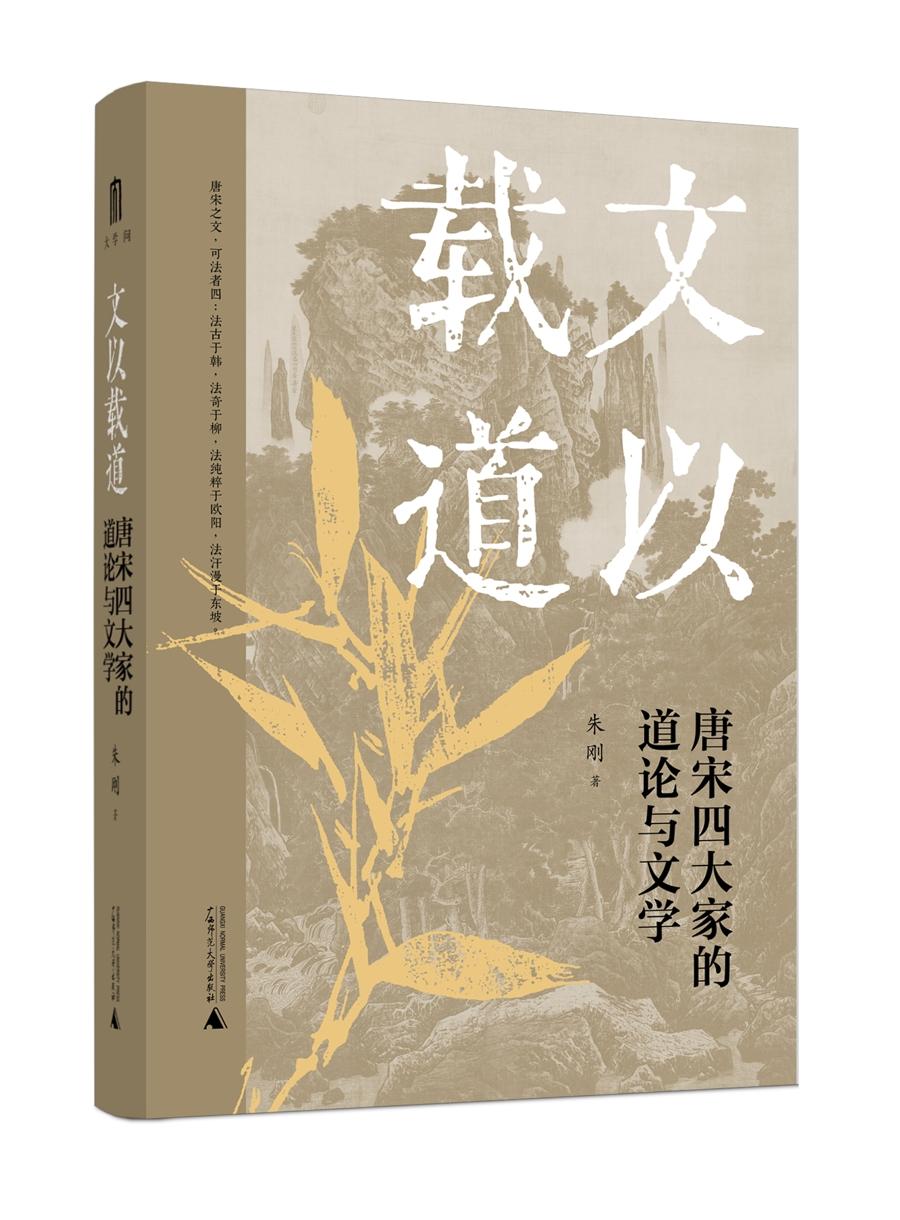
《文以載道:唐宋四大家的道論與文學》,朱 剛 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內文選讀:
載道vs.言志:從韓愈、歐陽修、蘇軾看道學、士氣和古文盛衰與共
總之,中國古代文論中並無“載道”與“言志”的對立;唐宋古文家講“文以載道”,其“道”實指本其“所學”而獨自樹立的一家之言,與“言志”恰爲同義;而唐宋古文大家之“所學”,雖有不出儒道之範圍的侷限性,卻更重在自出新意。因此,“文以載道”的實質,是要求在文學創作中貫注理性精神。理性精神在文學領域的崛起,當然與宋學“主理”的傾向一致,它有可能給文學帶來一些損失,因爲理性思維可能會過濾掉某些詩性的智慧,但從更廣的歷史視野來看,它標誌着我國先人在思維領域的一次革命,也標誌着他們對文學的思考進入了一個更爲自覺的時代。從這個意義上說,“文以載道”的主張,不僅沒有抹殺文學的獨立性,反而增強了文學的獨立性。因爲文學的真正獨立,並不繫於某種“純文學”之觀念,而是根本地來自士人立說持論的獨立精神,這種精神,只能在一個士氣甚盛的時代纔會被認可爲當然。從中唐士人激於世變,奮發自立始,到北宋時代,士氣之高漲爲歷史上所罕見,其間雖隔了唐末五代宋初的一段“論卑氣弱”之時期,但一直有人與衰頹的風氣相抗爭,至歐陽修、范仲淹一出,以“道”自立的士風又被激揚起來,終宋之世,蔚爲大觀。所以,文學的盛衰,並不像周作人虛構的那樣,由“載道”與“言志”兩種對立的文學觀所導致,而是由士氣之盛衰所決定。士氣盛則文盛,“道”對於宋代文學的繁榮,是通過它激發士氣來貢獻其作用的。
唐宋古文的興起,是古文運動的成果;唐宋道學的興起,是儒學復古運動的成果。這兩個運動本是同一個,所以,道學與古文可謂孿生的兄弟,在以後成長的過程中,他們也沒有失去血肉的聯繫。道學的演進,表現爲“道”概念之含義的不斷豐富,從“善”而推究到“真”,又走向“美”,這個過程在韓、歐、蘇三家道學上表現得極爲典型;古文的發展,則表現爲不同的藝術風格的相繼出現,因爲此種“成體”“載道”之古文是以“道”爲靈魂的,所以“道”的含義的豐富,亦必對於藝術風格之形成產生影響,這裏仍取韓、歐、蘇三家爲例來說明。
錢鍾書先生《談藝錄》論李賀詩歌的風格,用了很多比喻,並將李賀與韓愈、蘇軾對比:
此非昌黎之長江秋注,千里一道也;亦非東坡之萬斛泉源,隨地湧出也。此如冰山之忽塌,沙漠之疾移,勢挾碎塊細石而直前,雖固體而具流性也。
這些比喻都極爲精彩,深得談藝之三昧。錢先生在這裏提及韓、蘇,是拿他們做比照,來凸現李賀詩歌的獨特風格,但所用的兩個比喻,卻極形象地概括了韓、蘇古文的藝術特徵。“長江秋注,千里一道”,是形容韓文氣勢之盛大,浩浩蕩蕩,一瀉千里,內容既豐富,而行文亦充滿力度。這當然與韓愈自己的藝術追求相符合,《答李翊書》所謂:
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
這種“氣盛言宜”的境界,是其學養到了一定程度的產物,而“長江秋注”的藝術風格,則與其所表現的思想內容相統一。歐陽修的文章風格跟韓愈不同,這在蘇洵《上歐陽內翰第一書》中有很好的比較說明:
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自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
他指出韓愈文中含有大量的險怪內容,而其盛氣足以駕馭之,使人震懾,不敢迫視。歐陽修的文章就不同了,他充滿自信,平易地講說着,語氣委婉而道理窮盡,一點兒不感到困難,有一副“容與閒易”的態度。歐陽修雖然也主張行文要有“氣”,但是他的“氣”比較委婉平和,不像韓愈那樣高潮迭起,要把讀者一下捲進去;他是以更爲理性的態度來漸漸引導讀者走向他的結論,以理服人,以情動人,而不是以氣勢來挾帶人。歐陽修的古文,奠定了宋代古文流暢婉轉、平易自然的總體風格,他曾經通過曾鞏指點王安石,說:“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要王安石別模仿孟子、韓愈的行文風格,而以自然爲追求的境界。這說明,歐陽修的古文風格,是他自覺追求的結果。清代的魏禧在《日錄論文》中把歐文比喻爲秀麗的風景:“永叔如秋山平遠,春谷倩麗,園亭林沼,悉可圖畫。”的確,歐文很像這樣的風景畫。
至於蘇軾的“萬斛泉源,隨地湧出”,此語本是他對自己文章的評述,見於《自評文》一篇。那意思是說他蓄養充沛,悟性通達,故能隨意揮灑,觸處生春,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而表現一切內容都能得心應手,姿態橫生。對於這樣一種寫作的自由境界,後人當然歎爲觀止,但只能形容,而很難從文法上進行總結,劉熙載《文概》說:
東坡文只是拈來法,此由悟性絕人,故處處觸著耳。
蓋其過人處在能說得出,不但見得到已也。
東坡最善於沒要緊底題說沒要緊底話,未曾有底題說未曾有底話,抑所謂“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耶?
這些話說得都不錯,但一個學習蘇文的人恐怕很難從這裏找到門徑。蘇文的確多“拈來法”,的確能表達自如,也的確善於隨題生髮,但若學習者照此去做,看到什麼寫什麼,想到什麼寫什麼,拿着一個題目隨意說去,那恐怕並不能寫得好。倒是從後人學習蘇文失敗的教訓中,我們可以窺見蘇文的長處。《日錄論文》說學蘇易流於“衍”,《文概》說“東坡文雖打通牆壁說話,然立腳自在穩處”,這說明蘇文於表面上的泛衍外,內中自有精奧者存。據李之儀《莊居阻雨鄰人以紙求書因而信筆》一文記載,蘇軾作文時,並非提起筆來隨興而成的,他每每研墨甚久,下筆甚遲;據何薳《春渚紀聞》卷七“作文不憚屢改”條記載,蘇軾對於自己的詩文,也不以一時快筆爲定,而是勤於修改的。據此來看,蘇軾寫作時,運思頗爲精心。他少年時的文章,仍有推求、經營的痕跡,高下抑揚,務爲絢爛;中年以後,筆力足以稱意,才達到了隨物賦形,收放自如,而渾然無跡的境界;但到晚年萬里南遷之後,可能是受柳宗元詩文影響的緣故,又轉爲精純,不大再放筆馳騁,往往寥寥數語,而精神矍鑠,光彩照人,使弟子們歎服其略無老人的衰憊之態,原來寓於泛衍之中的精奧到這時才脫穎而出。因此,蘇軾的行文自如,本出於好學深思,其“萬斛泉源,隨地湧出”的藝術風格,是由剛健明銳的理性力量操縱而就的。他非但比韓、歐更爲博大,實亦更爲精深,非但更爲自由,實亦更爲果決。
這樣,韓、歐、蘇三人的藝術風格之形成,不僅出於他們個人性格上的偏好,而且無一不與各人的學養、自覺的追求和理性的思考相關。我認爲,他們在道學上的不同造詣,是與他們不同的文風相一致的。韓愈的“道”是一種文化價值之“善”,它對於人們的影響力來自列聖相傳的權威性,和某種拯溺救亡、力挽頹波的奮發感,以及“善”本身具有的激發正義感的作用。這樣的“道”,被認爲是由先聖傳下來,不幸中絕,需要人們重新高舉這個旗幟,把它光大起來的。所以,韓愈主張學“道”的人必須養成浩然之“氣”,學養並重,以盛氣來行文,才能帶動讀者進入聖人之道。於是,他的文風便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歐陽修雖也有激昂慷慨之語,但因爲他的“道”已從文化價值更推本於自然、人情之“真”,以“至理”的面目出現在文章裏,所以,他不必借氣勢壓人,而可以平心靜氣地擺事實、說道理,“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這樣,他的文風便會平易自然,流暢婉轉,而更具理性之風範。至於蘇軾,他的“道”已是造化中所蘊含着的“美”的“無盡藏”,這種“道”無處不在,所以觸處皆春;再加上他的“性命自得”的通達境界,遠大的“器識”和越來越深刻的對人生的反思,最終覺醒爲主體“性”的高揚,於是他的文風便不但有“萬斛泉源,隨地湧出”的揮灑之妙,並且能以理性的思致爲其精神,一步步脫落華飾,現出氣骨。如果我們以韓、歐、蘇三家爲道學和古文的三個發展階段,那麼,我們便能看到道學和古文同步發展的景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