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合花永遠芬芳——緬懷作家茹誌鵑 | 孫甘露 馬文運
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茹誌鵑以其獨特的創作風格佔據着重要地位。初登文壇,《百合花》就以精巧的構思,清新俊逸的美學風格,從平凡的生活中開掘出具有深刻社會意義的主題,受到廣大讀者及評論家的歡迎。十年動亂之後,《剪輯錯了的故事》又以犀利的藝術筆觸勇敢地對歷史進行了嚴肅的反思,首開“反思文學”先河。今年是茹誌鵑誕辰100週年,追溯她的文學創作,更是對她文學精神的緬懷與重溫。

茹誌鵑 徐福生/攝
年少初現創作才華
1925年10月30日(農曆九月十三),茹誌鵑出生在上海。她幼年家境貧寒,11歲才斷續接受教育,少年生活漂泊不定,充滿了艱辛與苦澀。但生活的磨難並沒有壓垮茹誌鵑,反而鑄就了她堅韌不拔的性格。
在艱難的環境中,她對文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常在空餘閱讀書籍,進而創作。茹誌鵑的第一篇作品《生活》發表於1943年11月22日《申報》副刊《白茅》三十六期上。這篇不足千字的作品,寫一個女大學畢業生謀生無門,憤而撕毀大學畢業文憑,在構思和寫法上初現關注自我、關注女性的端倪。
《生活》發表時,年僅18歲的茹誌鵑已隨兄參加了蘇中地區新四軍,投身革命的洪流之中。她先後成爲蘇中公學學員、蘇中軍區前線話劇團團員,華中軍區和華東軍區文工團組長、分隊長,創作組副組長等。在部隊裏,她經歷了戰火的洗禮,見證了戰士們的英勇無畏,也感受到軍民之間的魚水深情。這些寶貴的經歷成了她文學創作的豐富源泉。她往往在通宵行軍的間歇中,就着月光,墊着揹包,寫下歌詞、快板、廣場秧歌劇等作品。1947年,她寫的歌詞《跑得兇就打得好》,獲軍區文藝創作二等獎。1950年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了她新中國成立後寫的第一個短篇小說《何棟樑和金鳳》。1952年創作的話劇《不拿槍的戰士》,反映了復員軍人在礦山的鬥爭生活,榮獲南京軍區1955年頒發的文藝創作二等獎。

1950年8月31日起,《文匯報》磁力副刊(“筆會”曾用名)分九期連載了茹誌鵑的短篇小說《何棟樑和金鳳》
1955年7月,茹誌鵑從南京軍區轉業到上海,任《文藝月報》編輯,小說散文組副組長、組長,被吸收爲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會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又被選爲作協上海分會理事。
《百合花》:清新俊逸獨樹一幟
1958年,茹誌鵑發表了短篇小說《百合花》。這部小說刊發在當年3月的《延河》雜誌上。同年9月,小說被《人民文學》轉載,並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百合花》以解放戰爭爲背景,描寫了1946年某次總攻前夕,小通訊員送“我”到前沿包紮所支援醫護工作,後向一個剛過門三天的新媳婦借被子的故事。在借被子的過程中,通訊員的羞澀、質樸,新媳婦的善良、熱情,都被茹誌鵑刻畫得淋漓盡致。而在此後戰鬥中,通訊員爲了保護羣衆英勇犧牲,新媳婦則用自己的新婚被子爲他入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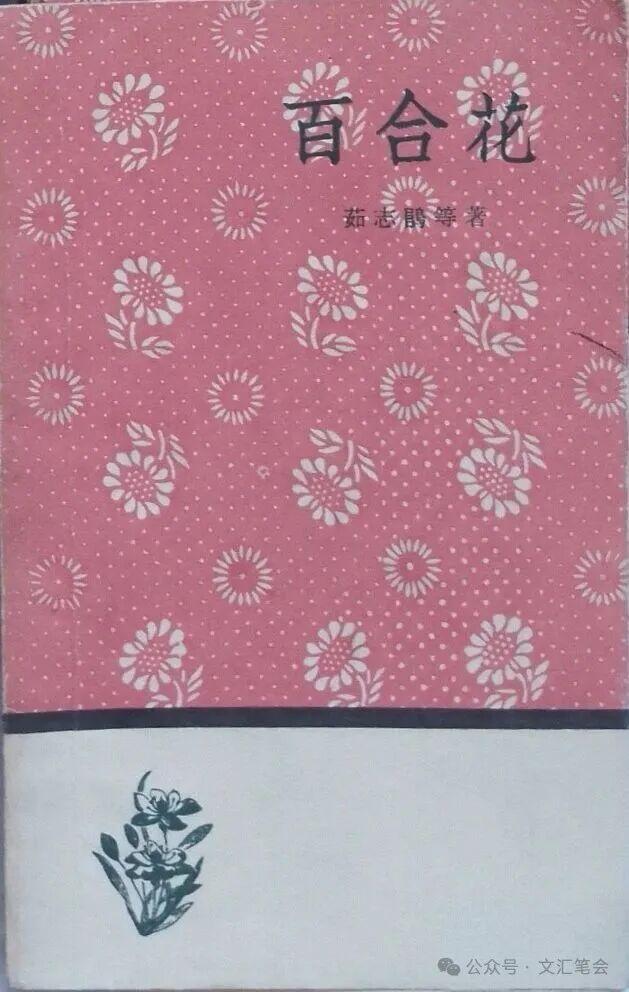
《百合花》第一次收錄在作品集內
《百合花》有別於當時描寫宏大戰爭、英勇戰士的戰爭題材小說,沒有直接描寫戰鬥過程,而是通過三個人的情感碰撞和相互交流,展現了戰爭中的人性之美和人情之暖。正如茹誌鵑自己所說:“把大東西漏了,小東西卻剩下了。”她以小見大,用一條被子、一個通訊員、一個新媳婦,折射出了整個時代的光輝。同時標題“百合花”的意蘊豐厚,一方面,它指的是被子上的“百合花”,是實實在在的圖案;另一方面,它又象徵了年輕媳婦的樸實美麗、純潔無瑕。此外,更象徵着小通訊員與新媳婦的美好心靈,更象徵着這種超越了人世間一切血緣親情的軍民間最聖潔最美好的感情。
《百合花》發表後以其獨特的魅力受到了讀者們的熱烈歡迎,也引發了評論家的熱議。茅盾在《談最近的短篇小說》一文中以兩個“最”來形容自己看到這部小說的感受:“這是我最近讀過的幾十個短篇中間最使我滿意,也最使我感動的一篇。它是結構謹嚴、沒有閒筆的短篇小說,但同時它又富於抒情詩的風味”,並用“清新、俊逸”來肯定茹誌鵑的創作風格。侯金鏡指出了作品的整體特點:“色彩柔和而不濃烈、調子優美而不高亢”;“對人物感情的客觀描繪和作者注入到作品裏的自己的感情,兩者統一起來,就形成了委婉柔和、細膩優美的抒情調子”。
由於創作上的突出表現,茹誌鵑於1960年離開編輯崗位,成爲中國作協上海分會的專業作家,有了更多的時間進行創作,她的創作進入高峯期。1959年茹誌鵑出版了第一個短篇小說集《高高的白楊樹》(上海文藝出版社),收集了此前的10篇短篇小說和5篇特寫。1962年出版了第二個短篇小說集《靜靜的產院》(中國青年出版社),收集了1959年至1962年創作的10篇短篇小說。

茹誌鵑第一個短篇小說集《高高的白楊樹》(1959)
1961年5月至7月,中國作協上海分會先後四次舉行茹誌鵑短篇小說創作討論會,會後侯金鏡、王西彥、魏金枝等評論家分別在《文藝報》1961年3期、7期、12期發表了《創作個性和藝術特色——讀茹誌鵑小說有感》《有關茹誌鵑作品的幾個問題》《從題材多樣化談起》《也來談談茹誌鵑的小說》等多篇文章,從茹誌鵑作品的題材與風格的關係,和人物創造等方面開展熱烈討論,一致肯定茹誌鵑在創作上取得的成就和小說的藝術風格。
宏大敘事融入日常生活
茹誌鵑的作品不追求宏大敘事的波瀾壯闊,也不刻意塑造高大全的英雄形象,而是將目光投向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物。她在《追求更高的境界》一文中說:“我追求像那些前輩作家那樣,能在一個短短的作品裏,在一個簡單、平易的事件、人物身上,卻使人看到整個時代脈搏的跳動;一個普通人物的遭遇,卻能反映出整個國家社會的命運。”
《妯娌》中兩位媳婦同爲青年團成員,她們以“團員的原則”相處,互相謙讓、爭相爲國家作貢獻,讓婆婆對妯娌失和、最終分家的顧慮成了“多餘”,從家庭關係變化反映了革命理唸的滲透。《魚圩邊》並不通過政策宣講或集體勞動的宏大場面展現“農業合作化”這一關乎國家經濟轉型的重大命題,而是聚焦於兩個渴望加入合作社的兒童爭相冒充社員的天真舉動。《里程》裏,在運河邊擺渡的王三娘從過去認爲擺渡是“替大家辦事”,心安理得地收下鄉親們的報酬(雞蛋、麥子等),轉變爲主動提出“不要錢”,並最終在風雨中奮力修好渡口的跳板,將其視爲自己對集體應盡的責任,反映的正是合作社運動時期,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精神如何逐步深入人心、改造個體思想的宏大歷史進程。
茹誌鵑筆下的人物鮮有傳奇色彩,多是些普通人:童養媳、新媳婦、老大娘、通訊員、文工團員……這些看似平凡的個體,卻承載着時代變遷的密碼。《在果樹園裏》中的童養媳小英,從家庭中出走,成長爲公社果園組組長,她的蛻變軌跡不僅是個人命運的轉折,更是新中國女性掙脫封建枷鎖、走向獨立的縮影。《如願》中的何大媽,帶着與兒子阿永共同的苦難記憶,在新時期經歷了母子間的隔閡與和解,她的喜怒哀樂映射着新舊社會交替中普通人的陣痛與適應。《春暖時節》的靜蘭,作爲家庭主婦因丈夫忙於工作而感到關係疏遠,最終通過參與福利合作社找到自我價值,她的經歷道出了時代轉型中女性對自我實現的渴望。

青年茹誌鵑
茹誌鵑寫的普通人也對“英雄”概念進行了豐富與拓展。《百合花》中的通訊員天真、淳樸、憨厚,與“我”同行時,“撒開大步,一直走在我前面”;問他是哪裏人時,“臉漲得像個關公,訥訥半晌”;來拿被子時,“繃了臉,垂着眼皮,上去接過被子,慌慌張張地轉身就走”。而他肩上的步槍筒裏插着的幾根樹枝,顯露出他對生活的熱愛與少年人的爛漫。但當敵人的手榴彈襲來時,他沒有絲毫猶豫,“撲在那個東西上了”,用身體擋住了致命的彈片。這個英雄迥異於同時革命題材小說中的典型英雄,他的英勇犧牲也是通過擔架員的轉述來完成的,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當時英雄主義基調和人物程式化的模式。
細膩入微的心理描寫,是茹誌鵑實現“以小見大”的關鍵技法。她捕捉人物最細微的動作、神情與心理波動,讓隱藏在表象之下的情緒自然流露。《百合花》中,新媳婦聽“我”解釋借被子的緣由時,“不笑了,一邊聽,一邊不斷向房裏瞅着”,這個細節既寫出了她的猶豫,也暗示了被子對她的特殊意義(是她的嫁妝);當她最終決定借出被子時,“看看我,看看通訊員,好像在掂量我剛纔那些話的斤兩”,寥寥數筆,將她內心的權衡與最終的覺悟刻畫得入木三分。《靜靜的產院》中譚嬸嬸的心理刻畫同樣精妙。面對荷妹的新做法,她“覺得有些不大入味”,後來又“有些生氣了”,“心裏還是悶悶的”,後來卻被荷妹的行爲打動,改變心態,主動學習,“眼前忽然豁亮起來”。這些複雜的心理活動,不僅塑造了一個真實可信的老一輩勞動者形象,更折射出社會轉型期人們面對新事物時的普遍心態——既有對傳統的眷戀,又有對進步的渴望。正是這種對個體心理的精準把握,讓茹誌鵑的作品超越了對時代的簡單呼應,達到了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統一。
女性視角觀照時代變遷
冰心最早注意到了茹誌鵑小說的女性視角。冰心在《一定要站在前面——讀茹誌鵑的〈靜靜的產院裏〉》中認爲當時的報道里、小說裏的婦女形象,也能感動人、教育人,“但是從一個婦女來看關於婦女的心理描寫,總覺得還有些地方,不夠細膩,不夠深刻,對於婦女還不是有很深的熟悉和了解,光明的形象總像是蒙在一層雲紗後面,不是那麼眉宇清揚,容光煥發。”而“茹誌鵑是以一個新中國的新婦女的觀點,來觀察、研究、分析解放前後的中國婦女的。她抓住了故事裏強烈而鮮明的革命性和戰鬥性,也不放過她觀察裏的每一個動人的細膩和深刻的細節,而這每一個動人的細膩和深刻的細節,特別是關於婦女的,從一個女讀者看來,彷彿是隻有女作家才能寫得如此深入,如此動人”!
茹誌鵑喜歡直接採用第一人稱講述故事,《阿舒》中的“我”是一個會講故事的女同志,“我”看到了阿舒這個天真可愛、活潑好動的少女。《高高的白楊樹》中的“我”是一個見習護士,透過“我”的眼睛寫張愛珍、小鳳兒及蔣月珍的故事。《三走嚴莊》中的“我”是一個年輕的女幹部,主人公收黎子的進步便是透過“我”的視覺來體現的。“我”化身成女戰士、女勞動者,深入周圍各種美好的女性,和她們談心,交朋友,從而更加酣暢地抒情。
茹誌鵑在作品中塑造了豐富多彩的女性形象。一類是美麗單純、充滿激情的年輕姑娘,這也是茹誌鵑作品中出現最多的一類女性,如熱情淳樸、把兔子當寶貝的小愛珍(《高高的白楊樹》);風風火火、一心撲在工作上的小何(《新當選的團支書》);敢於走出舊家庭,改變自己命運的小英(《在果樹園裏》);愛笑愛美、不知憂愁的阿舒(《阿舒》《第二步》)……她們大多剛剛步入社會,所經歷的工作、生活都充滿着關愛和幸福,所以她們總是帶着純潔天真、無憂無慮的心情來感受周圍的一切,持有對光明和美好的堅定信念。

茹誌鵑作品《關大媽》(1955)
還有一類是老當益壯、不甘落後的老大媽們。《關大媽》中的關大媽本是普通農村婦女,但當日本侵略者的鐵蹄踏入家鄉,她冒着生命危險掩護了游擊隊員們,被游擊隊員們稱爲“媽媽”。《如願》中的何大媽解放前愁柴愁米,解放後雖不愁了,“人卻還鎖在鍋子邊”。後來,她放着清福不享,熱心街道生產,從“鎖在鍋子邊”成爲生產組小組長,完成了自身的角色轉換,並且意識到了自己的價值和社會的關係。《靜靜的產院裏》的譚嬸嬸最後堅定地拿起了產鉗,在荷妹幫助下第一次成功完成了手術。譚嬸嬸並沒有因爲年紀大就靠邊站,而是努力成爲緊跟時代步伐的勞動女性,她的身上也因此煥發出了更耀眼的生命光彩。
這些女性人物在茹誌鵑筆下不斷成長,尤其是心理上的成長,展現出女性的社會價值,從而確立女性的自我價值。《三走嚴莊》中的收黎子在土改鬥爭、解放戰爭的鍛鍊中,由嫺靜、溫順的年輕媳婦,成長爲勇敢、幹練的支前隊長。《百合花》中新媳婦的成長則更具層次感,從最初忸怩羞澀,對來借被子的通訊員毫不客氣,讓他空手而歸;再到聽“我”說打仗是爲了老百姓的道理時,借出被子;最後當她見到犧牲的通訊員時,主動給通訊員擦臉擦手縫補衣服,並獻出那條撒滿百合花的新被子。這一過程中新媳婦逐漸理解了革命的意義,也完成了自我超越。
《剪輯錯了的故事》:首開反思先河
“文革”中,茹誌鵑的作品遭受的不再是溫和的批評而是直接的否定,她在《〈百合花〉後記》(刊於1978年9月17日《光明日報》)中提到“一會是‘中間人物’,一會兒是‘反重大題材’,‘反火藥味論’也有些象,‘無衝突論’也搭點界”。可是這種攻擊性的批判並沒讓她再次焦慮,十年停筆的沉澱讓她的創作心態越發成熟。她寫道:“這是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世界觀。我願意他們存在下去,因爲他們有存在的價值”,“文學作品的質量有高低之別,而不存在重大與渺小之分”。
1979年,茹誌鵑創作了短篇小說《剪輯錯了的故事》,大膽地突破禁區。這部小說通過農民老壽的視角,批判了脫離實際的極左政策和官僚主義對基層生活的破壞。這部小說首開“反思文學”大潮。小說採用“時空交錯”和“碎片化剪輯”的敘事手法,打破了傳統線性敘事的框架。以老壽的心理活動爲主線,通過現實與回憶、真實與幻覺的交替呈現,將不同時間節點的場景並置:把革命戰爭年代幹羣間肝膽相照的魚水深情,和“大躍進”時代的不正之風,以及老壽想象中的未來戰爭的場面,有機地交錯和間隔,不僅增強了文本的張力,更讓讀者直觀感受到歷史斷裂帶來的心理衝擊。這部小說也充分顯示了茹誌鵑在表現手法和藝術構思上的創新。
之後,茹誌鵑又相繼創作了《草原上的小路》《兒女情》《家務事》等一系列作品,對“十年動亂”的前因後果進行了更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草原上的小路》寫草原石油城兩個年輕人的愛情故事,揭露和譴責某些幹部官復原職後,把人民羣衆甚至曾經共患難的老戰友、老同事、老部下的疾苦和冤屈統統置諸腦後,只求保住自己的“烏紗帽”。《兒女情》中的革命老媽媽田井在丈夫早逝後憑一己之力把兒子撫養成人,晚年時她唯一的心願,就是安排好兒子的工作和生活,可是兒子卻並不完全認可母親的這一片好心。《家務事》中“我”的家庭雖然沒有經歷坐牢批鬥之類的遭遇,但是一家人也是天各一方,丈夫支援小三線,大女兒去插隊,“我”要去幹校參加“鬥批改”,留在家裏的只有八歲的小女兒淘淘一人,反映了這場動亂帶給每一個家庭和每一個人的災難。
這些小說描寫的都是日常生活,卻直接、明顯涉及社會生活中某些重要的激烈的矛盾衝突。茹誌鵑在《漫談我的創作經歷》中認爲,“在任何社會里,超脫於政治、經濟以外的,單純的家務事、兒女情是不存在的,”因爲“每個人的命運都在那裏發生變化,每個人命運的變化都跟國家的大事相關聯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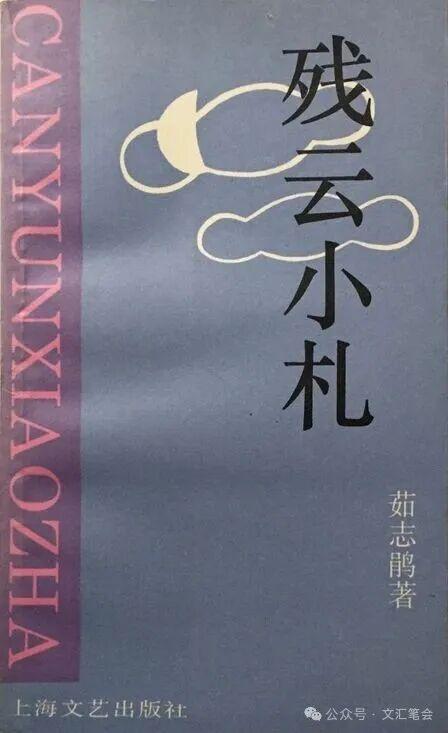
茹誌鵑生前最後一本作品集《殘雲小札》(1998)
評論家黃秋耘以“從微笑到沉思”概括茹誌鵑此時的創作變化:“她的目光變得更加敏銳,她的視野更加開拓,觀察也更加深刻了。她對過去各個歷史時期的生活積累中的種種複雜的矛盾進行了嚴肅的思考,她無畏地面對現實,以犀利的藝術筆觸勇敢地去剖析、挖掘和鞭撻。”
全心全意爲年輕人鋪路
1985年創作完《喜筵》之後,茹誌鵑的工作重心慢慢轉移到中國作協上海分會的工作中去。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第四次會員大會後,她擔任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兼《上海文學》副主編。鄧友梅在《阿姐志鵑》一文中寫道:“我曾問過她,幹嘛要擔任這工作,這會影響寫作的。她說,我想爲年輕人創造點條件,叫他們早點出來,他們有才能缺少經驗,要有人幫助解決困難才能闖出一條路來,我願爲他們鋪路。”
1985年,在茹誌鵑的主持下,中國作協上海分會從上海工廠調進來四位有才能的年輕人,分別是:作家趙長天、劇作家宗福先、評論家吳亮、評論家程德培。爲此《新民晚報》記者還連續四天開設專欄“作協新來的年輕人”,專訪四位青年作家、評論家。
同時,茹誌鵑很重視培養上海地區的青年文學愛好者。1985年她拍板創辦了以學習班形式召開的“上海青年作家創作會議”,邀請全國著名作家、評論家來給上海青年作者上課,領全國風氣之先,也促使金宇澄、阮海彪、殷慧芬等一批青年作者脫穎而出。

茹誌鵑(右)與張煒(左)、周介人(中)
茹誌鵑多年一直致力於培養青年作者,早在20世紀50年代她在《文藝月報》工作時,就開始深入基層,發掘新人。她耐心細緻地幫助青年作者,從談素材、構思,一直到修改具體作品,推出了許多優秀的作品。她還是上海市工人文化宮工人寫作學習班的輔導員。1971年,上海熱處理廠的青年工人宗福先因哮喘病發請了八個月長病假,利用這段時間他學着寫了一篇反映當時自己工廠生活的小說《政策》。經人介紹,他把厚厚一沓小說稿送到茹誌鵑家裏。時隔不久,茹誌鵑來到宗福先家,親手交還稿件,同時對作品做了批評:“你根本不懂怎麼創作,37萬字的小說都沒有一個完整的故事。”但之後話鋒一轉:“你年紀那麼輕就有這麼好的語言,你還有自己的想法,對當時的社會表達了一種不同的看法,有這兩條你就可以走上創作的道路。”宗福先感動不已,心裏有了方向。
1978年,鐵凝創作了小說《夜路》,被人推薦給茹誌鵑。茹誌鵑敏銳地發現了鐵凝的文學才華,把《夜路》發在《上海文藝》當年第5期的頭條上,併爲小說撰寫了一篇評論《讀鐵凝的〈夜路〉之後》,對這篇小說給予極大的肯定,這也是國內第一篇鐵凝小說的評論。
在茹誌鵑培養和關注的衆多青年作家中,最令她驕傲的應該是女兒王安憶。她奉行“不去管她,讓她自己去探索,去走路”的原則,任憑女兒在文學道路上馳騁。1980年,茹誌鵑的《剪輯錯了的故事》與王安憶的《誰是未來的中隊長》分別獲1979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1979年第二屆全國少年兒童文藝創作二等獎,傳爲佳話。此後,王安憶相繼創作出《小鮑莊》《本次列車終點》等中短篇小說,《長恨歌》《富萍》《天香》《考工記》《一把刀,千個字》《兒女風雲錄》等長篇小說,她的作品十多次榮獲國內外重要文學獎項,其成就得到國內外文學界的廣泛認可。作爲中國文壇中鮮有的母女作家,她們在文壇具有持續且深遠的影響力。
文學潮流不斷髮展,茹誌鵑作品的魅力仍然不減,多部作品被譽爲紅色經典,被廣泛選入各種教材;她筆下的人物形象,依然鮮活地存在於讀者的心中。就像一朵盛開在文學殿堂的“百合花”,茹誌鵑的作品散發出淡雅而永久的芬芳。
來源丨文匯筆會
編輯丨蔣竹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