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怪物之名直擊你的心魔——膽小者慎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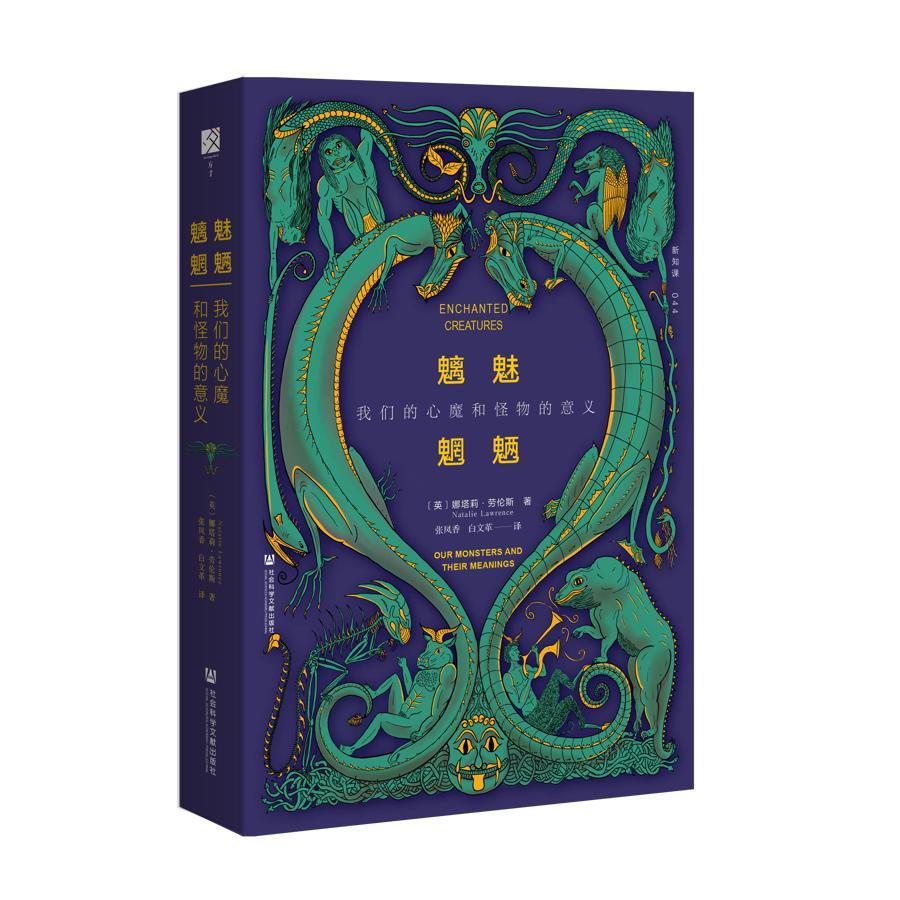
《魑魅魍魎:我們的心魔和怪物的意義》,[英]娜塔莉·勞倫斯 著,張鳳香 白文革 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一部深入探索人類與怪物之間複雜關係的文化史與心理分析著作。作者娜塔莉·勞倫斯以跨學科的視角,從史前洞穴壁畫中的獸人巫師、古希臘神話中的彌諾陶洛斯,到《聖經》中的蛇與混沌之龍,追溯了怪物在人類想象中不斷演變的形象與象徵意義。
通過剖析不同文化中的怪物敘事——從冰河時代的薩滿儀式到現代科幻中的異形——勞倫斯帶領讀者思考:爲何人類始終需要怪物?它們如何幫助我們面對生命的無常、死亡的恐懼以及自身潛藏的黑暗?
>>內文選讀
15世紀博學家萊昂納多·達·芬奇在其筆記中曾給藝術家提出了這樣的建議:“如果想讓幻想動物看起來真實——比如我們假設它是一條龍——那麼,讓龍的頭部借鑑獒犬或塞特犬的形態,眼睛像貓眼一樣明亮而深邃,耳朵如豪豬的一般小而圓短,鼻子參考格力犬般細長,眉毛如獅子那般整齊濃密,顳骨像老公雞那樣輪廓清晰,而頸部則像水龜一樣自由伸縮。”達·芬奇的這一繪畫訣竅歷久彌新,許多怪物的形象都是動物特徵的巧妙拼貼。龍,作爲最原始的“烏爾”怪物,融合了爬行動物、鳥類、貓科動物和魚類的特質。1979年電影《異形》中的異形(Xenomorphs),是兼具哺乳動物的優雅、昆蟲般的關節和兩棲動物溼潤皮膚的獵食者。它們會吞噬你的面孔,並將你的軀體作爲孵化室——就像馬蠅或幾內亞線蟲,如果它們體型增大千倍,也會做出同樣的行爲。自然界中本就充滿着難以想象的生物。觀察螞蟻面孔的微距攝影,就可發現那些刀片般的剛毛、冷酷的複眼和工業化的顎部。或者目睹紐蟲捕食,它會突然伸出與身體等長的黏性線狀口器,來捕捉獵物。用現有的存在稍加想象便能創造怪物。
我們的生活與其他動物息息相關。我們一直在狩獵它們、畏懼它們、食用它們、觀察它們、模仿它們,與它們協作,並對它們深深着迷。因此,動物自然也存在於我們的幻想之中,構成了我們創造的大部分素材。它們是我們自身存在的活生生的參照物,我們用它們來象徵自身的品質:獅子代表勇敢,驢子代表固執,孔雀代表虛榮。引用人類學家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的一句著名的話,動物對“思考有益”。而怪物對思考甚至更加有益。
我們常將其他動物稱爲“creatures”(生物)或“beasts”(野獸),然而,這兩個單詞的字面含義並不等同於“animals”(動物)。它們深刻揭示了人類與其他物種之間的複雜關係。拉丁語動詞“creare”(創造)在中古英語中演變成了“creature”(被創造之物)。《牛津英語詞典》將“creature”定義爲“區別於人類的動物”。而《劍橋詞典》則將其定義爲:“一種不尋常或虛構的生命體”。《韋氏詞典》則羅列了多重定義:“無論是否具有生命,被創造的生物可以是低等動物、人類,或是自然界中具有異常或不確定性特徵的存在”,以及“一個依賴於他人或作爲他人工具的實體”。作爲“Creaturely”(受造物)則意味着它們不僅要按照人類的奇思妙想所塑造,還要屈從於人類的意志。

“beast”(野獸)這個詞同樣趣味橫生。《牛津英語詞典》追溯了該詞是如何從拉丁語的“bestia”演變爲古法語中的“beste”,並自中古英語時期以來一直保持爲“beast”的歷史。它既可以指“與人類相對”的動物——無論是“家養的”還是“大型或危險的四足動物”,更被賦予了道德評判的隱喻色彩:形容那些具有“野蠻或桀驁不馴”特質的人,或是“令人反感或不悅”的人或事物,甚至是指“極端殘忍、暴力或墮落”的行爲。我們把不願面對的自我,冠以野獸之名。
儘管我們不願承認,但人類同樣是具有獸性的生物,擁有與其他生物一樣殘忍、暴力和墮落的能力,甚至可能更甚。我們是動物中的一員,有着有機生命體不可避免存在的侷限性。這種認識讓我們感到不安,正因如此恐怖生物纔會在我們的想象中橫行。文化人類學家歐內斯特·貝克爾描述了我們的動物本性如何激發了我們的文化:“現實世界是如此可怕,以至於人們不願承認。現實告訴人類,他們不過是些微小而戰慄的動物,終將衰敗和死去。”文化中的“幻覺”爲我們提供了逃避的途徑,使“人類顯得重要,對宇宙至關重要,在某種程度上是不朽的”。文化使我們能夠創造生活的神話,使存在變得更加容易;它幫助我們構建世界,使其更易於管理。一方面,我們創造神祇,給予我們永生的希望。另一方面,我們製造並驅逐怪物,以將自身的獸性推開。
我們所創造的許多最重要的怪物,都源自那些我們既獵殺又害怕被其獵殺的動物。美國作家大衛·奎曼指出:“時有可怕的食肉怪獸如厄運般自森林或河流中出現,噬人血肉”,這意味着“人類最早的自我認知之一,便是意識到自己不過是肉軀”。狼、老虎、鱷魚、熊、獅子以及其他偶爾會殺死併吞食人類的動物,不僅是危險的存在,更是殘酷現實的印證。人體轉瞬即淪爲食物。我們通過將這些奎曼所稱的“頂級掠食者”神話化爲神祇,或者貶低爲怪物來應對它們的威脅。如今,我們消滅了它們中的大多數。
數千年來,西方學者和神學家都試圖區分“人類”與“動物”。關於“是什麼讓我們與衆不同?”的答案隨着歷史的變遷而演變:從神聖的優越性和靈魂的擁有,到複雜的語言、自我意識和抽象思維。我們建立了文明準則,以堅定地壓制我們思想和行爲中更爲野性的部分。我們將自己置於所有其他生物之上的等級制度的頂端,並編織了複雜的神聖秩序神話來強化這一觀念。從亞里士多德伊始,“自然秩序鏈”(Scala Naturale)或“偉大的存在之鏈”(Great Chain of Being)就主導着西方對自然世界的認識。它將人類置於僅次於上帝和天使的位置,其他生命形式則按照複雜度遞減的順序排列在人類之下,從鳥類和哺乳動物,到爬行動物和兩棲動物,再到昆蟲和帶殼生物。在上帝與一羣卑微野獸之間,人類唯一的明智之舉是向上:竭力與“低等生物”劃清界限,向神聖的境界艱難攀升。
正如自然哲學家梅蘭妮·查林傑所言,“一萬年的現代性”造就了一種“拒絕承認自己是動物的動物”。或者,我們也可以說,這是一種不願將自己視爲動物的動物,卻持續憂慮着自身與動物的區別。我們強調諸如自我意識等我們認爲是人類獨有的特質,以此將自己與自然界區分開來,同時試圖壓制那些傾向於動物本性的自我部分。然而,切斷我們與生物性的聯繫,也使我們與有機世界及其賦予我們的一切重要元素疏遠。這讓我們變成了不完整的存在,不斷抗拒着野獸般的“他者”。怪物形象的歷史反映了我們對動物本性的矛盾情感和需求,它們是這種複雜關係中的傷痕碎片,也可能成爲修復這種關係的關鍵。

關於那些徘徊於人類與動物之間的微妙界限上的“怪物”,我想要探討的內容遠不止這些。這些“怪物”涵蓋了諸如“鬍子女士”這樣的遊樂場奇觀,以及其他各類展覽品;還包括對種族和國家的誇張且令人不安的諷刺描繪;更有因發育障礙而遭受詆譭的人們,以及我們與類人猿和其他靈長類動物之間的關係。這是一個充滿政治與社會複雜性的領域,常常與權力和帝國的運作緊密相連,需要以一種獨特的方式來處理。
本書深入探討了那些塑造了我們的思想、社會以及自然認知的怪物形象:這些是我們與之共存、共思考的生物。我們從混沌與創世的傳說開始,直至我們對《啓示錄》中末日及其災難性怪獸的幻想,完成了一個完整的循環。從最早的藝術作品到最新的媒體表現,我們將追溯人類想象怪物的歷史。我們將看到,儘管我們周圍的世界在幾千年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人性基本上沒有太大的改變。現在,當人類與自然的關係處於懸崖邊緣時,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理解這些怪物。
膽小者慎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