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風之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這種話也只有皇帝會說 | 李榮



我家小李上小學和初中的時候,他臨睡前我們都會朗聲讀會兒書,一者助眠,二者大家在睡意朦朧中多少會記得一點所讀書的模糊印象,以後與書“再打照面”時能夠說一句“倒像在哪裏見過”,也就可以了。後來小李長大了,沒太多機會全家再湊一起讀書了。但這個習慣我們夫妻倆倒保留了下來,如今臨睡前依然要讀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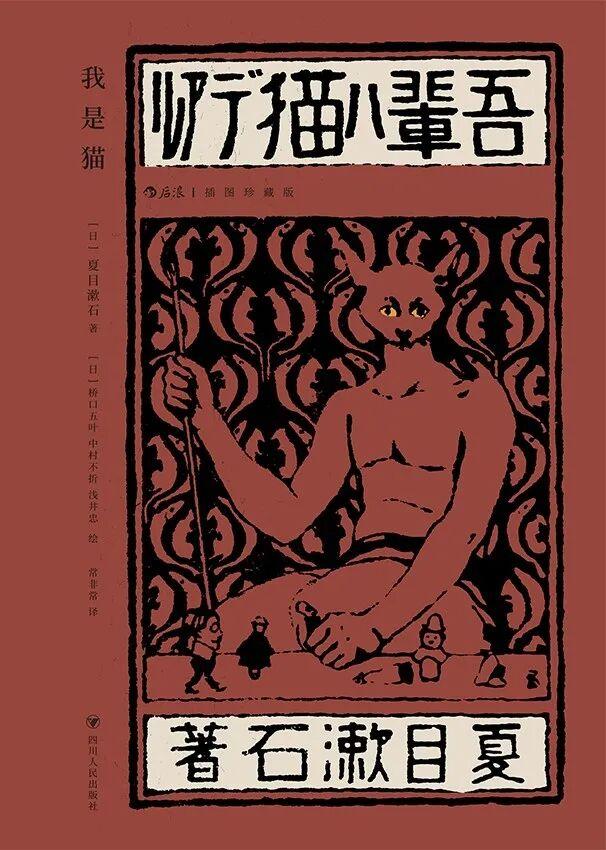
目下手頭在讀的是夏目漱石有名的小說《我是貓》,到了收尾的第十一章,述及在苦沙彌的家裏,他的兩位好友獨仙和迷亭,邊下圍棋邊閒扯,一位指對手一着棋是死路一條;對手不以爲然,橫下一條心,非走這一着不可;那一位就給他接上一子兒,隨口就吟出了一句唐人的詩句:“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看到這一句,我當然眼熟。兩年前我出版了一本自己的集子,取名《南風之薰》,還專門作了一篇序文,其中就引用了這一句。此次讀到,如見故人。
《我是貓》的譯本在這一句下加了一個譯註:語出《舊唐書·柳公權傳》。唐文宗夏日與衆學士聯句作詩。文宗的首聯是:“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作:“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一讀之下,馬上發覺與我當初序文裏的引用有出入:一是“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與“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這兩句,我序文裏都用上了,但分在了兩處,因爲我以前的閱讀裏,這兩句是從兩個來源而來。“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由閱讀王船山的文章而來;“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是由方回的《瀛奎律髓·夏日類》中而來,卻不知道這兩句其實是同時同地“一唱一和”的聯句,舊唐書是最初的出處。二是“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之句,舊唐書裏是唐文宗之詠,而我的序文因方回《瀛奎律髓》中的“唐太宗之詠也”,帶出一句“歷史上亦算明君的唐太宗,有時候不恤民情有如此”。
有出入,當然立即細細查究;一查之下,只恨自己讀書少。文宗與柳公權的這兩句君臣“聯句”,其實是歷史上廣爲人知的“熟典”,不知其出處,應該是有點慚愧的。而那個因照抄方回之誤而誤的“唐太宗之詠”,也早就有人詳詳細細地指出過,明清的馮舒、查慎行、李光垣等好多位,都曾在評點中特別提到:文宗,原訛作太宗。我的序文曾經在文匯筆會上以《“南風吹來清涼”》爲題刊登過。筆會有個好傳統,只要它所刊載的文章裏有差錯或可商榷的地方,便專門闢出“迴音壁”的欄目,作爲切磋交流的園地。只是一般的迴音,都是別人指出作者的錯誤,這回我卻是來“自首”,應該算壁上第一人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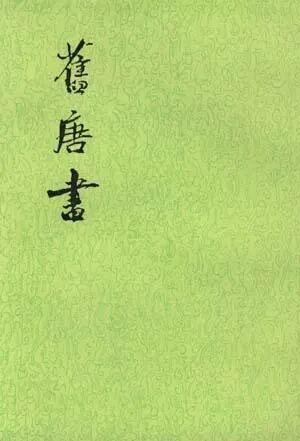
文宗與柳公權的那個“熟典”,出自《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五的列傳第一百一十五,原文是這樣的:
文宗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丁、袁五學士皆屬繼,帝獨諷公權兩句,曰:“辭清意足,不可多得。”乃令公權題於殿壁,字方圓五寸,帝視之,嘆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焉!”
它在歷史上有名,是因爲大家覺得柳公權在文宗身邊,沒有像宋玉給楚襄王來上一篇《風賦》那樣,讓文宗也明白,普通的百姓庶民哪有你這樣的條件,覺得炎熱的夏天也自有夏天的微涼舒暢。比如東坡,就作過一詩《戲足柳公權聯句》,詩前的小引就說到了宋玉:“宋玉對楚王,此獨大王之雄風也,庶人安得而共之。譏楚王知己而不知人也。柳公權小子與文宗聯句,有美而無箴,故爲足成其篇。”足成的後四句曰:“一爲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意思是同爲炎夏,居所不同,苦樂也不同,而且讓人感嘆的是,不僅苦樂不同,苦樂更是難以相通。所以,如有炎熱裏的“清陰”,能夠“均此施、分四方”就好了。
不過,細細品讀舊唐書裏的那段文字,也難說柳公權的言下沒有“微諷”之意——他特意拈出“殿閣”兩字,或許意謂微涼只應“殿閣有”,庶人的茅屋“安得而共之”。只是文宗又是點贊其辭,又是點贊其字,讚不絕口,即便柳公權實有諷諫之意,也早被文宗的讚歎之聲轉化成一片和和美美的氣氛。也有後代文士看出柳公權的言外之意,但還是怪他沒有如宋玉對楚王那樣“隨事納誨,以啓主心,而達下情”。所以東坡的“足句”依然有續成的必要,不作“隱躍含糊之語,冀幸一悟者”。
另外,方回在《瀛奎律髓·夏日類》的卷首小序中,雖然訛文宗爲太宗,把唐代皇帝也搞錯了,但整個小序的意思,與東坡是一致的:“南風之薰,以解民慍,以阜民財,舜之詠也;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唐太宗之詠也。所處之時同,而所感之懷不同。故宋玉有雌雄風之對焉。”可怪的是,清朝有名的大學問家、四庫全書的總纂紀昀紀曉嵐以及他的大弟子,指出了文宗太宗的訛誤,卻說此序“殊無謂”。
這個評語加得有點重,我讀了覺得很是驚訝,不知如何來評點這麼一個“點評”。紀昀是高人,不至於讀不懂或讀不通方回這麼的一小段話。即使紀昀有自己不同的想法,卻也沒必要下一個“無謂”的判語,這本身亦甚無謂。紀昀似乎對方回特別沒有好感,曾經說:“文人無行,至方虛谷(方回,號虛谷)而極矣,周草窗之所記,不忍卒讀之。”周草窗即周密,宋末元初有名的學者、詞人,與方回是同時代人。周密的《癸辛雜識》,在《汴梁雜事》篇中有《方回》一則,記錄了時人對於方回的“十一可斬”之說。這“十一可斬”的說法,也是由方回的一則醜行而來。當年賈似道當道時,方回“暱於”賈,賈勢敗,就上書言賈“十可斬”。時人取笑他,賈“十可斬”,你方回“十一可斬”,比賈還多可恨的地方。紀昀由其爲人而及於其詩評,大體上沒有好印象,認爲他的《瀛奎律髓》,“非盡無可取,而騁其私意,率臆成篇,其選詩之弊有三:一曰矯語古淡;一曰標題句眼;一曰好尚生新”。
不過,今人看古人,還是儘量人歸人、文歸文、詩歸詩、選歸選、評歸評。方回的《瀛奎律髓》能夠流傳至今,自有他的價值。他選詩的隻眼獨具,他論詩的高見卓識,都不應該輕易地抹煞。雖然其中也有紀昀所指出的強調枯瘦古淡、雕句琢眼和新奇生硬的弊病,但同時他也知道要修正和補偏,認爲“詩先看格高而意又到、語又工爲上;意到、語工而格不高次之;無格、無意又無語下矣”,格高易流於粗獷生硬和枯澀,須濟以細潤圓熟和豐腴。這樣的詩評理論應該是比較完整的。
方回這樣的人物,在生活行事上庸俗甚至可恥的地方很多,但同時“傲倪自高,不修邊幅”,肆意揮灑。寫“夏日類”小序那一小段時,不在意“是文宗還是太宗”這樣的細小處,完全能夠想象。甚至,很有可能是他想傳達出“偉大如太宗,尚且如此”的意味,欲抑先揚,潛意識作祟,直把文宗作太宗。當然,這只是我的推想,更不是我因爲“照抄不誤”而因錯出錯的藉口。
【南風之薰】是李榮在筆會的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