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愛編程,仍可熱愛寫作



在裝置作品《我熱愛編程,害怕寫作》中,一系列舊型號計算機、遊戲機在展廳中依次排開,字句不斷在跨越年代的屏幕上湧現。藝術家周蓬岸用自己青少年時接觸過的這些設備,因“機”制宜地編制了不同的文本生成程序,使它們儘可能仿照自己的文風生成出各異的文本。有的運用原始的模板拼貼,有的則藉助互聯網接入了時髦的語言大模型,不同的原理和迥異的輸出,用不停息的文本光標,撫慰了那個熱愛編程而害怕寫作的少年的心。
如果說這一作品是藝術家的自我療愈,那麼在新近出版的《機器如何學會寫作》一書中,作者丹尼斯·伊·特南則爲上述作品提供了歷史的參照。這位曾經的軟件工程師將“自動寫作”描繪爲一種古已有之的“衝動”,從古代阿拉伯學者的占卜用具談起,認爲機器用於語言文字處理的歷史已有上千年之久,而運用一系列規則以產生詩歌韻文,更是一種古已有之的“技術”。在他的敘述中,無論是從語法上下功夫,將其轉換爲一系列的形式化規則;還是發明各種“模板”和“定式”,以加快消遣讀物和劇本的生產;又或是普洛普對民間故事中敘事要素的發現,都與自動寫作存在歷史的關聯,共同體現了把寫作外化爲機器裝置的意圖。他還發現,前人運用雙關和多義詞提供意義晦澀而又引人聯想的文本,這種“技巧”亦爲後世的人工智能所繼承。如20世紀60年代問世的早期聊天機器人ELIZA所給出的回應讓人誤以爲感興趣,實則只是重複着一些固定模板的話術。

《機器如何學會寫作》,[美]丹尼斯·伊·特南 著,耿弘明 譯,東方出版中心2025年出版
爲人工智能尋找早期淵源,這樣的敘事隨着公衆對人工智能愈發關注和好奇,已變得流行起來。在它們所提供的表面聯繫和貌似深刻的“思維方式”共通性之外,不由引人追問:爲人工智能編織不爲人所知曉的某種“前傳”,究竟是有益於人們對當下的人工智能建立更加深刻的認識,還是爲了解歷史過往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不幸的是,在大多數時候,這類敘事都只是將過去種種思想和技術的發明,表現得彷彿就是爲了達到今天“人工智能”的狀況。這樣一種“輝格式”的方式意味着在上述兩個方面無法提供洞見。一方面,它始終是以當下的狀況爲標準,評判並選取是哪些“思想”“發明”推動了人工智能的發展,哪怕在歷史情境中,這些觀點和事物的提出者也並不以文本生成甚至自動寫作機器爲目標。說古人的占卜策筮是一種“自動生成”,無疑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歷史實際。另一方面,挖掘、追認現代人工智能的古代前驅,也有悖於它表面上援用的“媒介考古”研究方式。用埃爾基·胡塔莫和尤西·帕裏卡在《媒介考古學:方法、路徑與意涵》中給出的表述,媒介考古的目標恰恰在於構建“媒介被壓制、被忽視和被遺忘的另類歷史”,而從過往追溯人工智能的“來時路”,總是難免會預設對當下狀況的肯定。
幸運的是,特南並沒有陷入這樣的窠臼。他可貴地引入了修辭學視角,指出當前將人工智能擬人化甚至神化成某種決定性的力量,是通過將工具“移動到句子的主語位置”來完成的。正是因爲獲得了這樣一個語法上的位置,機器才能夠進行“檢測、設計和掌握”,並因此獲得了“行動主體感和內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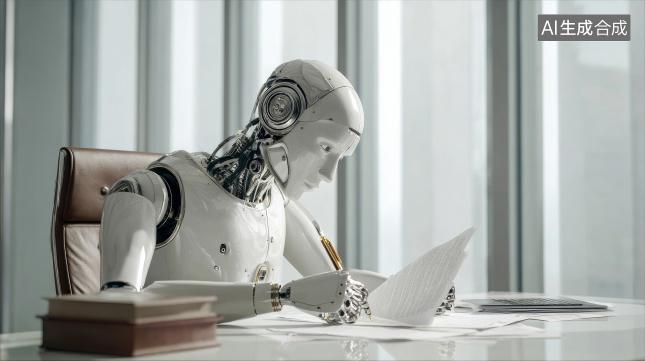
圖源:視覺中國
特南指出,以機器爲主語,並不是“自動寫作”的必然要求,而是人們在接受和認識人工智能時不自覺地授予它的。有許多因素引導我們這樣做,但特南認爲,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來自人工智能的開發者對於自身責任的撇除:“通過在語法上讓算法來掌權,研究人員就撇清了他們自己應有的責任——也就間接剝奪了我們人類在(自動寫作)這件事上的能動性。”將人工智能“置於主語”意味着隱匿其中人爲因素的影響,並將這種人爲因素僞裝成機器的能動性。另一方面,普通的使用者接受了這種修辭,也就意味着不自覺地讓渡出了自己的能動性,從而在人工智能面前陷入被動。
如此,本書中譯本副標題“給人工智能的文學理論”也就獲得了另一重意涵:它號召一種“爲”(for)人工智能境況而新構建的“文學理論”。這種“理論”並不將有關自動寫作的想象與設計勾連起來,彷彿要“量體裁衣”式地專爲人工智能“定製”,而是對流行的有關人工智能的言說加以分析,特別是從修辭上予以審視,從而揭示被有意掩蓋或轉移的關鍵矛盾與問題。它有效地將前者難免浮泛的類比,轉換爲後者的批判性力量,以此用“文學理論”來回應“自動書寫”引發的困擾。在本書中,作者用九個引向結論的必要觀念結束全書,尤其對人工智能背後的集體勞動、分佈性與隱喻性質、對責任的掩蓋等方面展開的有力批評,就是這種批判性意識的充分顯現。

圖源:視覺中國
但僅僅如此,仍然是不夠的。對機器展開技術原理的描述,儘管掌握起來存在一定的困難,但已有明確的規程。相比之下,對自身“使用機器”的經驗給予恰如其分的言說,卻缺乏類似的方式。對人文學者而言,或許有必要進行書寫或言說的並不是機器本身,尤其不是它們“是什麼”,而是使用機器的那個人自己,闡明機器所做、所行之事對自己又有什麼意義。換句話說,相比於機器對於“文學理論”的“技術實現”,製造和使用機器的“人”更適合成爲“理論”的關切對象。或許,一種真正面向人工智能境況的文學理論,其主要任務就應在於提供替代性的策略,以令使用者可以審視自己與機器交互的過程,進而引導機器的特定行爲。人的意圖以此得到明確的表達,並能用它覆蓋人工智能研發機構設計意圖中祕而不宣的那一部分。
由此我們不妨回望《我熱愛編程,害怕寫作》這件作品。就它本身而言,或許仍是躲避用文字表達自我的產物,但它在同時也表明,程序和機器未嘗不是人表達自我的可行途徑。可以說,這一作品的誕生本身就證明,編程已經成爲了一種創作方式、一種替代性的人類“寫作”。儘管“害怕寫作”,藝術家仍然選擇了這種替代的方式,其中突顯出無法抑制的對創作的渴望,纔是歷史上那些“自動寫作”背後真正欲求的事物。在那些湧現着文本的屏幕背後,在貌似空洞無物的程序運行之下,不僅有着人對編程的熱愛,而且歸根結底是人的無法“自動化”的創作欲,彷彿命令一般,在驅策着人們尋求與技術條件相匹配的表達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