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人文筆錄】要言不煩、深入淺出的貝多芬指南 | 楊燕迪



貝多芬,一個響亮的名字——即便他是異邦日耳曼人,即便他所從事的職業是“作曲”這樣一個音樂圈之外大家並不十分熟悉的“行當”,但貝多芬這個人物在中國(以及全世界)無疑享有極高的知名度。想來這是在情理之中。回想2020年,當時德國隆重紀念三位同在1770年降生於世的重量級文化人物誕辰二百五十週年:哲學家黑格爾、詩人荷爾德林、作曲家貝多芬。在我的印象中,貝多芬紀念的影響力和輻射面顯然超過另外兩位——這當然是藉助貝多芬音樂在當代演出市場、傳媒渠道和網絡平臺上的頻繁曝光率。可以說,貝多芬的聲名幾乎每時每刻都在我們身邊迴響,而他的作品的感召力二百餘年來似未見絲毫減退,至今仍保持着對專業音樂家和衆多樂迷的強烈吸引力。

路德維希·範·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年)
對於中國文化界和知識界,貝多芬的名字自20世紀上半葉開始通過傅雷先生迻譯的羅曼·羅蘭《貝多芬傳》而廣爲人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貝多芬作爲音樂藝術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受到高度重視,他的諸多重要作品頻繁亮相,而1959年爲慶祝新中國成立十週年,由著名指揮家嚴良堃指揮中央樂團上演貝多芬《第九交響曲“合唱”》(其中第四樂章的“歡樂頌”等唱詞首次用中文演唱)並在多個城市巡演,一時成爲盛事。及至改革開放,貝多芬在中國的接受度更是幾近“家喻戶曉”。除大量現場演出外,學術研究和圖書出版也適時跟進,以滿足大家對於鑑賞和理解貝多芬的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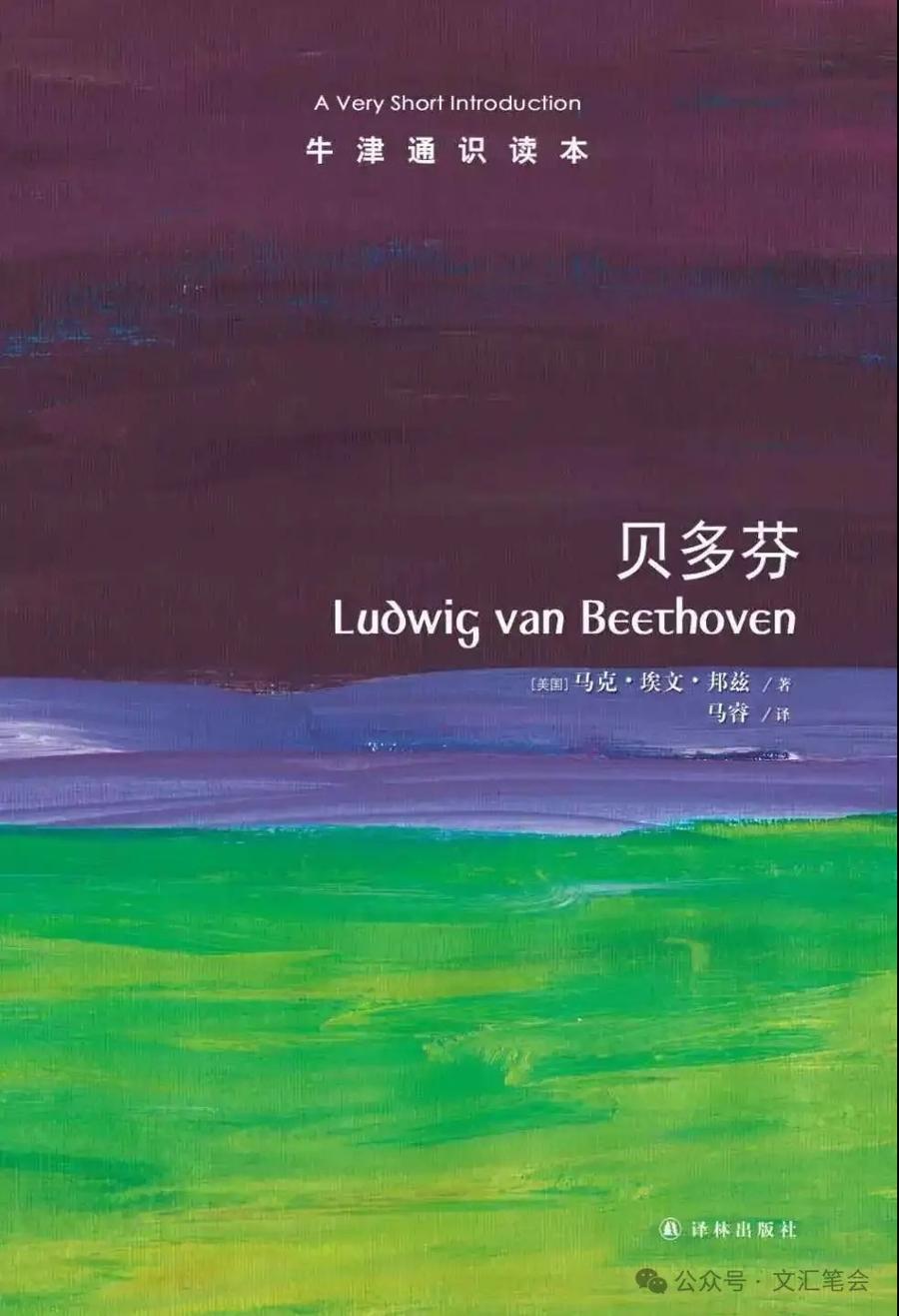
擺在讀者面前的這本《牛津通識讀本·貝多芬》中譯本(馬睿譯,譯林出版社2025年10月第一版),是國人接受和理解貝多芬的又一個佳音。它篇幅短小,要言不煩,且體例安排獨特,文筆深入淺出。作者馬克·埃文·邦茲(Mark Evan Bonds, 1954—)系著名音樂學者,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榮休教授,除《西方文化中的音樂簡史簡史》這部已有中譯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的通史性論著外,還深耕貝多芬研究、交響曲研究、音樂觀念史研究等專門化學術領域,著有《無言的修辭:音樂形式與演說隱喻》《貝多芬之後:交響曲中的原創性命令》《作爲思想的音樂:在貝多芬時代聆聽交響曲》《絕對音樂:一種觀念的歷史》《貝多芬綜合徵:將音樂聆聽爲自傳》等論著。不出所料,這位學者背靠自己深厚的學術積澱和熟稔貝多芬研究語境的優勢,爲“牛津通識讀本”系列帶來了簡明、別緻而有效的貝多芬理解指南(順便提一句,貝多芬是納入“牛津通識讀本”系列論述對象的唯一音樂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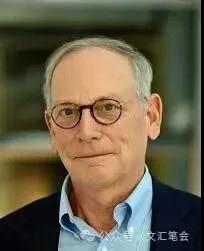
馬克·埃文·邦茲(Mark Evan Bonds, 1954—)
與一般讀者所習慣的“作曲家介紹”不同,此書絕非任何尋常意義上的“傳記”讀物。作者在簡短的“引言”中即申明“本書不是傳記,也沒有按時間順序展開”。他明確反對頭腦簡單地將作曲家的個人生平與其作品之間直接關聯,並警告“不要太急於將我們從他的音樂中聽到的情感等同於他的個人感受”。隨後在第一章“怒容”中,作者質疑19世紀以來將音樂作品當作“作曲家自我表達”的聽賞習慣,提醒這是貝多芬去世之後方纔形成的特定聽賞範式,並提倡以更爲多元和全面的視角、而不僅僅以“滿臉怒容”的“英雄形象”來理解貝多芬。這分明是受到了現代藝術和美學的觀念影響,傾向以更具客觀性和分析性而非印象感受式的方式來觀察、體驗和思考具體藝術家及其創作。
於是,作者以“怒容”“生平”“理想”“失聰”“愛情”“金錢”“政治”“作曲”“早期—中期—晚期”“音樂”“‘貝多芬’”爲標題,分十一個章節來框定自己的論述。讀者一看便知,這不是歷時性的敘事,而是對特定個別範疇的“橫剖面”式專題考察。這些專題不僅觸及貝多芬的生活紀事,也涵蓋他的創作發展與作品解讀,尤其“抓眼球”的是書中專門論及貝多芬的藝術理想、政治態度、失聰病痛、愛情經歷和經濟收入等話題,讓我們從不同的視角和途徑切入和走進這位作曲家的生存環境和內心世界,不僅滿足讀者對貝多芬生活各個側面的好奇,也爲聽者更有針對性地理解貝多芬的作品提供助力。

貝多芬《第三交響曲》手稿:包括封面上著名的被劃掉的獻給拿破崙的獻詞
書中諸多細節都體現出作者冷靜分析式的現代學術態度。如第二章“生平”伊始便是針對貝多芬留存至今約2000封書信、139本談話簿、8000餘頁樂譜手稿及相關作曲家日記等“一手資料”的清晰介紹,以及關於貝多芬生平諸多“僞證”的客觀澄清。作者關於貝多芬的人生準則、道德原則和藝術追求的論述,雖着墨不多,但相當深入透徹,從中可見貝多芬之所以成長爲這樣一個具有強烈現代精神的藝術家背後的思想、倫理和美學動因(第三章“理想”)。與之緊密關聯的是貝多芬的政治態度(第七章“政治”),作者在觸及這個課題時,幾乎是不動聲色地分析和坦陳貝多芬的矛盾心態——他針對拿破崙既崇拜、又鄙視的搖擺;他作爲一介平民藝術家,與貴族贊助人之間既親近、又排斥的複雜關係;以及他與當時的維也納當局既有表面合作、又有暗中博弈的有趣史實。
至於貝多芬生平的其他方面(如失聰過程、情愛經歷和收入狀況等),作者總是基於切實的史料辨析,清晰給出得體而謹慎的看法,從不言過其實,也嚴正拒絕道聽途說。例如,作者根據明晰的史料記載,簡要梳理並清晰交代貝多芬失聰這個頗具悲劇性的病痛歷程的重要時間節點及其影響(1802年寫下著名的《海利根施塔特遺囑》,1812年急劇惡化,1818年不得不依賴筆談本與他人交流,等等),並認爲“可以斷言的只有一點,那就是他的殘疾幫助他——事實上是迫使他——用一種非常罕見的視角來看待自己的藝術”。又如,針對貝多芬的“永恆的愛人”究竟是誰這一傳記研究中的著名難題,作者經過簡明的文獻分析後的謹慎建議是“兩個最有可能的候選人是安東妮·布倫塔諾和約瑟菲娜·馮·不倫瑞克-戴姆-施塔克爾貝格”,並闡述了1812年7月那封寫給“永恆的愛人”的神祕信件(是否寄出,還是被退回,當今學界仍有爭議!)對於貝多芬的深刻情感意義和隨後對創作的影響(直接與聲樂套曲《致遠方的愛人》Op.98相關)。再如,貝多芬通過自己的專業活動(創作、演出、出版和教學等)及通過貴族贊助獲得收入,作者對這些情況進行扼要梳理,不僅讓今日的讀者清晰瞭解貝多芬的生活狀況,也籍此呈現當時維也納音樂生活的典型狀態。凡此種種,都讓貝多芬作爲一位“凡人”的存在更爲全面豐滿,也更加真實可信。

安東妮·布倫塔諾(1780—1869,左圖)和約瑟菲娜·馮·不倫瑞克-戴姆-施塔克爾貝格,1779—1821)
當然,讀者之所以對貝多芬感興趣,不僅因爲歷史中存在這樣一位人物,更是由於這位人物的音樂至今仍在不斷鳴響,仍在感動現時現刻的你、我、他。順理成章,我們必定對貝多芬究竟是如何創造音樂的過程感到興趣。作者在第八章“作曲”中不僅梳理了貝多芬以“速記簿”記寫音樂的習慣和當前學界手稿研究的概況,還深入淺出地介紹貝多芬作品中諸如變奏、對位、迴旋曲式、奏鳴曲式、幻想曲等音樂創作的手法與形式,以及樂譜出版和修訂的相關細節——這是有意“放下身段”的音樂普及文字,但並不因此降低專業品格。第九章“早期—中期—晚期”進一步深入,雖沿用了傳統學術中的貝多芬創作分期共識,但以作曲家的絃樂四重奏爲核心舉證,說明各個分期的音樂特點,同時也對分期本身的合理性和其中的問題進行論說。在第十章“音樂”中,作者首先思考了貝多芬作品中的“標題”之於作品表現內涵的意義,隨即用簡明而清晰的筆調帶領讀者瀏覽貝多芬涉獵的所有體裁領域(交響曲、單樂章管絃樂作品、協奏曲、鋼琴奏鳴曲、室內樂、變奏曲、絃樂四重奏、聲樂作品、歌劇和教堂音樂等)——這種瀏覽因篇幅所限不免顯得蜻蜓點水,淺嘗輒止,但作者仍不失時機加入一些有趣的史實背景和音樂點評,從而讓讀者有意外驚喜。此章最後甚至觸及了當前世界樂壇中方興未艾的“歷史知情表演”(historically informed performance)潮流在當下語境中處理貝多芬作品表演的課題,可謂考慮周全。
在當代的文化語境中,沒有“接受史”的維度就不是完整的藝術理解。看來作者邦茲完全認同接受史之於貝多芬理解的重要意義,因而他在最後一章中追溯了貝多芬身後至今紛繁複雜到令人有些眼花繚亂的接受史軌跡。用帶引號的“貝多芬”作爲這一章的標題,作者意在強調,接受史中的“貝多芬”是帶有強烈時代印跡的“貝多芬”,每一代人、每一段歷史、乃至每一個國度和區域,都會帶着各自不同的眼光和需要來認識和“挪用”貝多芬——柏遼茲、李斯特、瓦格納、勃拉姆斯等後輩對貝多芬的推崇,德國民族主義的興起,納粹德國和盟國的對抗,東西方“冷戰”對峙,民主自由精神的當代弘揚,乃至現今藝術、電影、流行歌曲和大衆商品中貝多芬意象的“無孔不入”——在這位作曲家逝世至今的近二百年中,貝多芬可謂無時無刻不在影響着人類的政治、社會與文化,這是他的音樂和人格一直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明證。
關於貝多芬,有說不完的話語,道不盡的論題。多少年來,有關貝多芬的論著和文字之多,稱得上汗牛充棟。而這本短小精悍、簡明扼要的《貝多芬》,一冊在手,讓讀者迅速統攬全局,也不失洞察幽微,足見作者的用心和功力。願中國讀者通過此書走近貝多芬,願貝多芬的音樂繼續激勵、感動和撫慰我們的身心!
2025年8月20日寫畢於滬上書樂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