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水 |《金銀器的春秋》小引



一
金銀器研究,是由現代考古學的發展而催生。因爲金銀器不具備高雅的品味,歷來不入鑑賞與收藏,自然可以由於式樣不時興而被銷熔,另外打製新樣,或索性製成金鋌銀錠,收藏性質的傳世品中便鮮有清代以前之物。如果沒有考古發現的大量實例,我們就很難僅僅依據文獻記載來真切瞭解構築侈麗奢華之生活的用器究竟何等樣貌。
隨着金銀器的不斷出土,許多相關的政治事件、歷史人物乃至重要的以及失載的史實也重現於世。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附體於“物”的主人往往揹負着或慘慼或悲壯的各種故事,乃至一座墓葬、一處窖藏,即可演述一部情節豐滿的傳奇。不過直面研究對象,核心問題仍然是:它本身是什麼,即它的名稱包括紋飾與用途畢竟如何,所謂“本土特色”,其要在此。本書擔負敘事功能的是金銀器本身,它以自己的造型和紋樣來講述生長它的時間和空間裏的故事。這個時間和空間,就是以數千年爲跨度的華夏大地。作爲外來工藝,在金銀器進入中土的第一個千年亦即夏至西周,今天能夠見到的遺存尚屬鳳毛麟角。至第二個千年,它方漸露崢嶸。真正形成本土特色並融入日常生活,則要到秦漢以後才逐漸完成,從此走向繁盛。
“金銀器裏的中國”,是出版社最初的命題。但這是一個太大的題目,便不能不有所取捨。斟酌再三,選定了各有代表性的三個時段作爲本書之三章,即唐代金銀器皿、宋代金銀器皿、明代金銀首飾。第一章以“西風吹渭水”標目,落墨卻在“西風吹渭水”之後,即異域元素與傳統紋樣和社會風習交匯融合的中土化進程。第二章“千花百草爭明媚”,意在約略概括宋代金銀器以使用的普遍而有百花競豔之繁茂,且形成“自一家春色”。第三章明代金銀首飾以《牡丹亭》中語作爲標題,“一生愛好是天然”,這裏的“好”,讀作好壞的“好”。美人所愛之“好”,自然也是金銀首飾設計與製作者的追求,於是在繼承前代的基礎上,發展爲金銀首飾的集大成。三章分別選擇不同的切入點,各有側重,而不採用平均分配筆墨的方式,主旨便在於金銀器進入中土後,如何在不同的社會潮流和風習之下成爲藝術及生活中的藝術。
夏丏尊曾爲賈祖璋《鳥與文學》寫過的一則題記,雖是九十多年前的文字,卻一點兒也不過時,因擇要引述在這裏:“壁上掛一把拉皮黃調的胡琴與懸一張破舊的無弦古琴,主人的胸中的情調是大不相同的。一盆芬芳的薔薇與一枝枯瘦的梅花,在普通文人的心目中,也會有雅俗之分。這事實可用民族對於事物的文學歷史的多寡而說明。琴在中國已有很濃厚的文學背景,普通人見了琴就會引起種種聯想。胡琴雖時下流行,但在近人的詠物詩以外卻舉不出文學上的故事和傳說來,所以不能爲聯想的原素。薔薇在西洋原是有長久的文學的背景的,在中國究竟不能與梅花並列。如果把梅花放在西洋的文人面前,其感興也當然不及薔薇的吧……民族各以其常見的事物爲對象,發爲歌詠或編成傳說,經過多人的歌詠及普遍的傳說以後,那事物就在民族的血脈中,遺下某種情調,呈出一種特有的觀感。這些情調與觀感,足以長久地作爲酵素,來溫暖潤澤民族的心情……事物的文學背境愈豐富,愈足以溫暖潤澤人的心情,反之,如果對於某事物毫不知道其往昔的文獻或典故,就會興味索然。”近年有不少學者把文本研究開拓爲物質文化研究,作爲本身就是“物質文化”的金銀器,對它的研究也不妨開啓一個反向的視角,即揭發在它成爲“物質文化”的過程中,是哪些“文本”即“往昔的文獻或典故”,亦即“酵素”在起作用。

二
對早期金製品的檢測分析,顯示出先秦時期金製品的技術發展脈絡,可以認爲,戰國時期與金相關的金屬加工工藝大抵有八種,即錘鐷、包金、貼金、鑄造、鑲嵌、錯金、鎏金和金珠(陳建立《中國古代金屬冶鑄文明新探》,科學出版社2014年)。那麼可知古代金銀器製作的幾種基本方法,先秦時代已大體具備。金銀器製作不需要多人的通力合作,因此往往規模很小,乃至以一人之力即可完成製作,也因此流動性很大,技術傳播方便而迅速。科技含量既不高,發展的空間便很有限,千年以來,就幾項基礎工藝而言,變化不大,製作工具也是如此。
工藝既不復雜,造型與紋樣的設計便顯得格外重要。用心觀察物象,從物象的變化預測吉凶,是上古以來的傳統。其時凡有所行動皆須占卜,即《漢書·藝文志》所謂“雜佔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趨吉避凶,推究鬼神意旨,器用紋飾的取材自然也與此密切相關,甚至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它是藝術創造的一個迸發點。《易·繫辭傳上》:“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下文又道:“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意即《周易》一書,就是象徵,便是模擬外物以喻義。這是闡述創制八卦的思維過程。如此意旨,也可以移用於制器的設計理念。《易》之成,是將具象的萬物轉化爲抽象的喻理符號;若制器,則是將具象的萬物轉化爲寄意的藝術形象。設計者必要有對物象的細微審視和準確把握,即所謂“制器尚象”。
與設計相關的詞彙,可以從古文獻中拈出“經營”與“意匠”。“經營”多用於工程營建,如《書·召誥》:“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但也頗以此指稱藝術構思,如詩文,如書畫,而又常與“意匠”合說。《文心雕龍·麗辭》“至於詩人偶章,大夫聯辭,奇遇適變,不勞經營”,此言詩文。杜甫《丹青引》“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淡經營中”,此謂繪事。蘇轍《石蒼舒醉墨堂》“經營妙在心,舒捲功隨手”,則雲書法。又有曾鞏《山水屏》,開篇雲“吳縑落寒機,舒捲光亂目。秋刀剪新屏,尺寸隨折曲。蒐羅得珍匠,徙倚思先屬。經營頃刻內,千里在一幅”。繪製摺疊屏風的山水,其構思與純粹的畫作自然不同,它要考慮特定的尺寸與陳設的效果,這裏所云“蒐羅得珍匠,徙倚思先屬。經營頃刻內,千里在一幅”,便很有設計的意味了。不必說,金銀器的造型與紋樣設計,也是與此相通的。
紋樣的傳遞並不同時伴隨觀念的傳遞。格里芬的形象先秦時期即進入中土,來通和多曲長杯都是唐代酒器中的寵兒,希臘神話中的海神也爲唐代紋樣增添新奇,但紋樣和器物原有的名稱並沒有隨之而來。宋人名之曰“滿池嬌”的蓮塘水禽也是遼代裝飾領域的流行紋樣,然而取意卻在於捺鉢制度中的“春水”,元代依然。至明代,則成爲吉祥圖案。佛教藝術中的化生、觀音、摩尼、寶塔,乃至拈花的菩薩手,轉化爲首飾中的裝飾紋樣,便都逐漸脫離了原初的語境,而成就爲新的藝術語彙。諸如此類造型與紋樣的設計與演變,是本書的重點。

三
張蔭麟《中國史綱》的《初版自序》說到寫書時爲自己懸了三個鵠的,前兩項是:“(一)融會前人研究結果和作者玩索所得以說故事的方式出之,不參入考證,不引用或採用前人敘述的成文,即原始文件的載錄亦力求節省;(二)選擇少數的節目爲主題,給每一所選的節目以相當透徹的敘述,這些節目以外的大事,只概略地涉及以爲背景。”本書便也援此先例作爲標準。

四
即將付梓之際,出版社提出可否改換書名使之上口。首先想到“金銀器的四季”,學友廉萍博士則認爲不若將“四季”易爲“春秋”。比較之下,“四季”似有節奏感,而“春秋”更富蘊涵,於是乎取了後者,遂成今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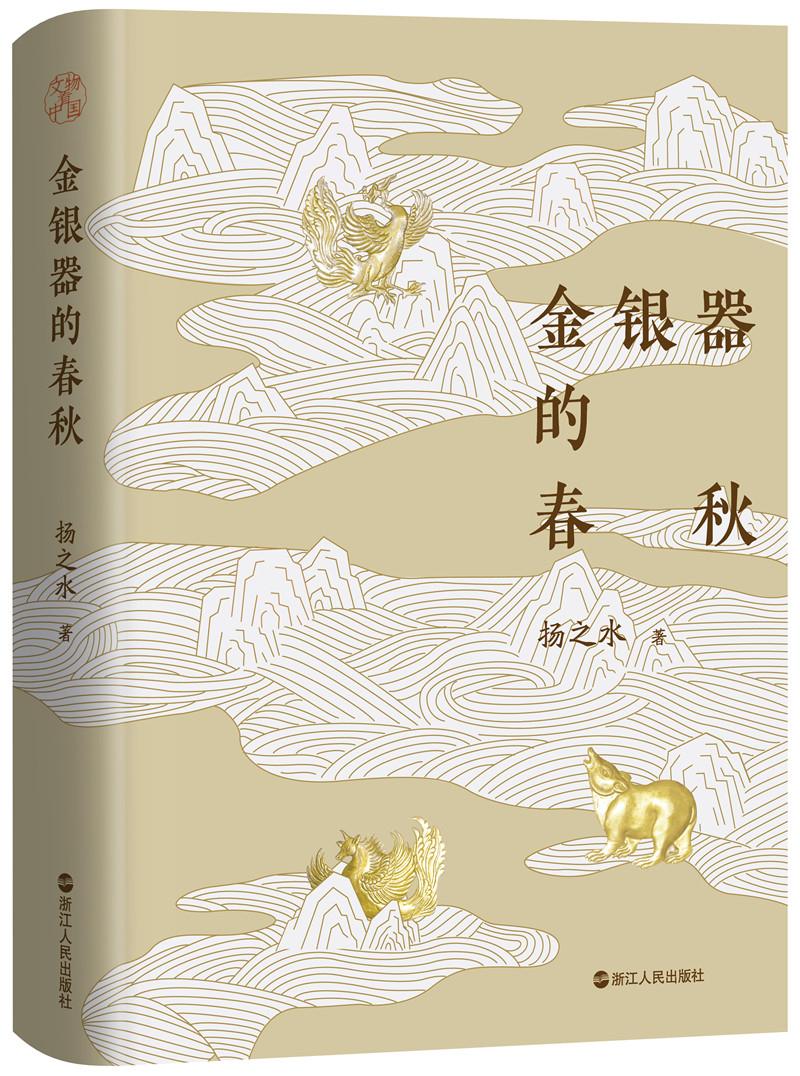
《金銀器的春秋》,揚之水 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