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酒僧到底是誰?你看《天龍》中哪位惡人活了下來,他曾爲僧爲道
如果一部作品給讀者的感覺總是“想一出是一出”,那它絕不可能成爲經典,甚至只讀到一半,你就可能會選擇齊書,作爲資深小說迷,你一定也遇上過這種情況。
而金庸的故事中固然也留下了諸多謎團,卻不會讓人有半路棄書的衝動,那是因爲金庸用十五部經典之作證明了他的故事中的種種情節都是有理有據的,他不會寫出那種毫無鋪墊的劇情。
不過在一部分讀者看來,《倚天屠龍記》中提及的“斗酒僧”就是個毫無鋪墊的角色,這人到底是誰?難道他真是空降的強者?答案或許並非如此。
一、金庸的伏筆
金庸的故事總會給人一種“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之感,那是因爲他在背景故事中加入了不少用於擴充世界觀的角色,同時在描寫登場人物時,他也會留下一定想象空間。

(僧人劇照)
比如《倚天屠龍記》中,當劇情發展到屠獅大會一節時,張無忌已然身懷四大神功,但他見到河間雙煞等人時,也曾發出過這麼一句感慨:“這八人的武功着實了得,實不在何太沖夫婦之下。除了三個是青海派外,其餘五人的門派來歷全然瞧不出來。可見天下之大,草莽間臥虎藏龍,不知隱伏着多少默默無聞的英雄好漢。”
又比如《天龍八部》中,當讀者都以爲天龍四絕,也就是蕭遠山、慕容博、鳩摩智以及蕭峯就是這個時代的天花板時,掃地僧悄然登場,一出手便驚豔了世人。
河間雙煞固然無法與掃地僧相提並論,但他們的存在卻證明了一個簡單的事實,那就是這武林之中還有不少未登場的高手,有何等高人都不足爲奇。

(慕容博、鳩摩智劇照)
不過就拿掃地僧這個角色來說,他的出現可不是毫無鋪墊的,他在防禦鳩摩智的殺招時,就提到對方所用乃逍遙派的小無相功,然而逍遙派的武功向來只有逍遙派門人知道,旁人哪怕是聽過“逍遙派”這三個字都難免被殺,可見這掃地僧以前多半是與逍遙派有些淵源的人,因此有人推測他是那逍遙派的創派祖師逍遙子,如此一來,就解釋得通了。
所以“斗酒僧的身份到底是誰”也一定能從書中找到合理的答案。
二、可疑的身份
嚴格來說,《九陽真經》這本經書是在《神鵰俠侶》中就已經被提及了,故事末尾的第三次華山論劍時,覺遠就帶着小徒兒張君寶登場,追捕瀟湘子與尹克西,他們的目的就是追回《九陽真經》,奈何那經書還是被那兩個賊人給奪走了。
直至《倚天屠龍記》中,少年張無忌才從猿腹中得到那經書,接着他便在那經書末尾看到了經書作者的生平事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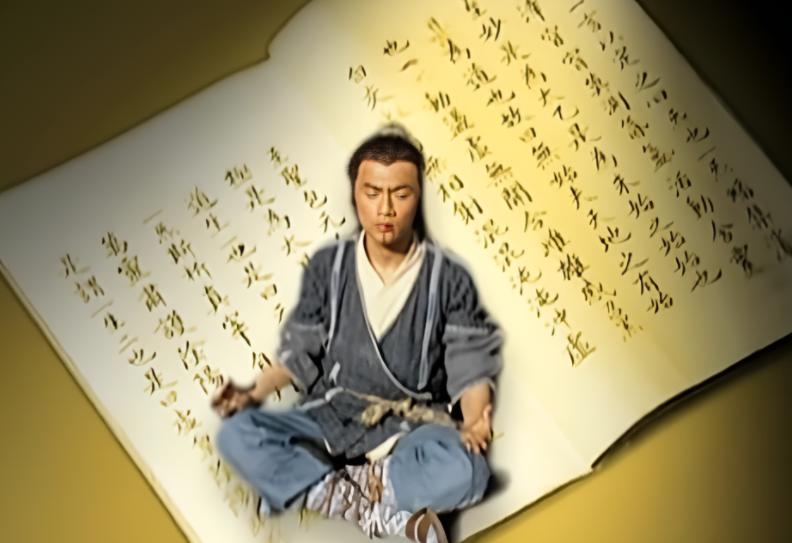
(張無忌練功劇照)
原著道:“他不說自己姓名出身,只說一生爲儒爲道爲僧,無所適從,某日在嵩山斗酒勝了全真教創派祖師王重陽,得以借觀《九陰真經》,雖深佩真經中所載武功精微奧妙,但一味崇揚‘老子之學’,只重以柔克剛、以陰勝陽,尚不及陰陽互濟之妙,於是在四卷梵文《楞伽經》的行縫之中,以中文寫下了自己所創的‘九陽真經’。”
從這段描述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這位斗酒僧的實力一定是在王重陽之上的,同時他還是個正派之人。
若你認爲他僅僅只是酒量好,那便大錯特錯了,試問歐陽鋒那大惡人說自己飯量好,要與王重陽比誰能喫,王重陽會和他比嗎?
毋庸置疑,所謂的“斗酒”只是讓王重陽能體面的輸給對方,對方一定是某位德高望重的前輩,並且實力遠勝於王重陽,王重陽纔會欣然答應對方“斗酒”的請求。
其中最關鍵的信息就是那僧人曾經也做過道士,所以那人會是誰?

(王重陽劇照)
有人說那人是虛竹,畢竟虛竹當過和尚,也當過僧人,但值得注意的是斗酒僧提到自己的經歷是先當的道人,後當的和尚,這恰恰與虛竹相反。
虛竹原本是少林派弟子,後來被無崖子化去了一身少林內功,這才入了逍遙派,甚至成爲靈鷲宮的主人,他的實力固然撐得起“斗酒僧”的形象,但經歷卻與斗酒僧不符,而天龍時代未被寫死的惡人卻符合這樣的形象。
三、改邪歸正之人
金庸筆下的惡人多半都不會被寫死,光是《天龍八部》中就有不少惡人直至故事結束都尚存於世,段延慶只是失蹤,慕容復淪爲瘋子,蕭遠山與慕容博則是被掃地僧點化,直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但他們的形象都與斗酒僧不符。
唯有“星宿老怪”丁春秋的形象能與斗酒僧對應上。
丁春秋原本是個十惡不赦之人,他欺師滅祖,還培養出了一羣殺人如麻的弟子,這種人死不足惜,奈何他的對手是宅心仁厚的虛竹,最終也只是在少室山一戰之後被留在少林寺而已。
丁春秋最後一次出現,就是原著第四十二回中,書中是這麼寫的:“丁春秋嗬嗬而呼,張大了口,虛竹手指輕彈,半粒藥丸飛去,送入他喉嚨。藥力一時未能行到,丁春秋仍癢得滿地打滾,過了一頓飯時分,奇癢稍戢,這才站起……丁春秋全身發抖,說不出話來。”

(丁春秋劇照)
這就是丁春秋在書中的最後一次登場,他被虛竹的生死符控制着,日後哪怕有機會逃出少林寺,多半也不會逃跑了,否則得不到虛竹定時送給他的解藥,他只會在無盡的折磨中死去。
可想而知,後來的丁春秋常年居住在少林寺中,多少會受少林僧人的影響,繼而改邪歸正也不足爲奇,而逍遙派中人向來追求不老長春之道,書中也提到丁春秋的樣貌宛如“神仙”一般,他能活到後天龍時代也實屬正常,那斗酒僧若是洗心革面的丁春秋,一切就說得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