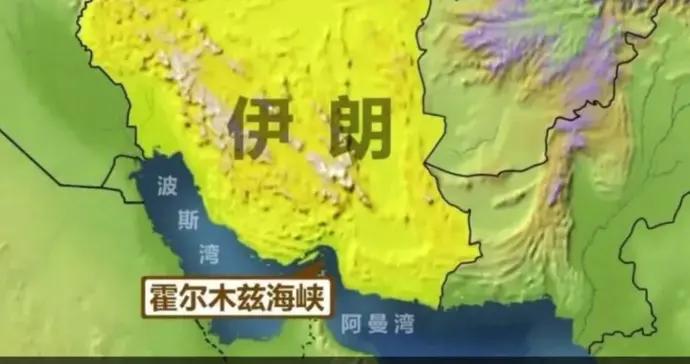《飛行家》裏有天空的浪漫與大地的現實



鵬飛執導的電影《飛行家》上映沒幾日,憑藉口碑逆勢上揚,貓眼預測票房上調近2000萬元。
這部中等成本影片,以獨特的風格辨識度,給觀衆帶來新的觀影體驗:作爲喜劇電影,它既跳出了開心麻花《夏洛特煩惱》《西虹市首富》等作品的東北爆笑喜劇類型化敘事框架,也區別於張猛《鋼的琴》東北工業喜劇的藝術表達路徑,開拓出一條兼具文學質感與商業潛力的新型喜劇電影敘事路徑。

“天空”意象和不同時代的互文式敘事表意
時代轉型與變革陣痛,素來是東北敘事電影的核心母題。
法國哲學家亨利·列斐伏爾在《空間的生產》中曾言,“社會空間是由空間的感知、表徵和生活構成的,它不僅反映了社會結構和關係,也影響着社會實踐和意識形態。”過往多數表現東北地域的影片,常以工業凋敝爲核心,借三重空間載體傳遞時代訴求,而《飛行家》則另闢蹊徑,將不同年代的精神特質凝練成三類特殊空間:天空、佐羅酒吧與東北平原的煙火日常,恰可對應列斐伏爾空間理論中的感知、表徵與生活三重維度。
其中,“天空”作爲影片最具辨識度的意象式空間,構築起一條浪漫敘事的核心脈絡。

天空的浪漫表意與主角李明奇的飛行軌跡相關,三次關鍵飛行串聯起電影中70年代青春突圍、80年代理想表達與90年代孤勇搏擊的敘事段落,也勾勒出他的人生底色:
70年代,孤兒李明奇與雅風的愛情漸入佳境,在徵得雅風父親這唯一長輩的許可、籌備婚姻之際,他對搗鼓飛行器、奔赴天空的渴望從未停歇。一場精心醞釀的高空飛行中,他循着老丈人畫下的圓圈,從2400米高空縱身躍下。
鏡頭以遠景與仰視視角鋪展,通過快速的蒙太奇剪輯,將李明奇成長的經歷、創傷和渴望通過飛翔突圍的內心狀態,融入自高空墜落的空間語境中,讓個體飛行與時代圖景相互映照。
此時的天空,既是可感知的物理空間,也承載着隱喻意義,打破了過往東北影像對地域空間的固有呈現。
80年代的飛行,多了煙火氣:應妻子雅風的要求,李明奇搭乘熱氣球升空,爲佐羅酒吧散發宣傳單,浪漫意象與商業訴求在天空中悄然交融。
而90年代的飛行,則成爲全片的收官重場戲:爲給妻子雅風的外甥小峯籌措醫藥費,李明奇鋌而走險,藉助飛行器從電視塔翼裝躍下,以孤勇姿態完成了浪漫與責任的雙重註解。

這三段飛行串聯起一條清晰的浪漫主義敘事線,李明奇每一次飛行的境遇與結果,都成爲推動劇情演進的核心線索。
圍繞“飛行”這一核心動作,影片還衍生出兩處極具象徵意義的特殊空間。
其一,是預備飛行前夕,熱氣球布料包裹下李明奇與雅風相處的私密角落,成爲二人情感的溫柔註腳;其二,是兩次地面降落點那五米見方的白圈,既象徵着安全與目標的達成,更暗合着“家”的精神內核。
這一圓圈意象,與影片中零星出現的唐僧師徒橋段,形成了微妙的隱性呼應,於不經意間豐富了空間的表意層次。
這五米之圈,是飛行家心中安穩的歸處。“去飛吧,李明奇”,雅風兒時的一句鼓勵,亦是託舉其逐風而上的力量。
個性及羣像:理想主義者的入世之姿
理想主義者形象,常是東北敘事電影中的靈魂人物。《飛行家》中的李明奇,同樣懷揣理想主義熱忱:無論是對飛行的執着追尋,還是對佐羅酒吧的用心經營,都藏着他對某種生命狀態的渴求。
與同類角色不同,李明奇的理想並非懸浮於現實的空想,他能飛亦能安於煙火,構築出富有個性的人物弧光。
影片對李明奇的塑造,跳出了情節與臺詞的直白勾勒,轉而以靜止的爆發力、肢體動作的小細節、眼神的情緒表現人物特殊狀態,貼合年代的美術氛圍與光影質感,讓人物自帶的“怪咖”氣質與獨特個性自然融入時代語境與人情事理之中,不顯刻意亦不突兀。

演員蔣奇明雖是第一次扮演東北人,但其與角色的契合度,達至“卯榫相扣”的境界:他自帶的鬆弛感與細膩勁兒,把李明奇在理想與現實間掙扎的複雜演繹得很到位,要不是其個人氣質融入演員表演的演繹,李明奇很難這麼活靈活現。
“能飛且能入地”,是李明奇理想主義的核心底色。
他並非沉溺執念、脫離現實的絕對理想主義者:第一次高空飛行,他隨隕石一同墜落,偏離了與未來岳父約定的五米白圈,便坦然收起飛行夢,退居家庭,安於凡俗日常;因在車間私自改造推送器不慎導致妻弟旭光受傷後,他便揣着滿心內疚踏實經營佐羅酒吧,以責任消解愧疚。
李明奇角色的“落地”還在於他的溫暖善良,長期照顧臥牀的岳父以及生病的外甥小峯,都是平凡日常的擔當。這份“明白什麼時候該飛,什麼時候該落”的清醒,讓他的理想主義不那麼“軸”,反而多了點入世的溫潤和人情味兒。
李明奇的入世姿態,還在與工友的羣像互動中得以深化。
影片並未將下崗職工羣體塑造成時代變革的“失敗者”,而是聚焦於他們骨血裏的良善與互助:當李明奇爲給小峯籌措醫藥費鋌而走險時,衆人紛紛籌措物資、傾力相助,呈現出困境中的溫情底色。
從70年代到90年代,東北傳統工業區深陷轉型陣痛,佐羅酒吧也始終在經營低谷中掙扎,而外國科研人員因熱氣球廣告尋至此處、歡聚一堂的段落,成爲羣像敘事的點睛之筆:
李明奇與雅風在熱鬧開心中流露的情愫渾然天成,工友間的協作默契自然流淌,既完成了一場極具感染力的重場戲,更以煙火氤氳的羣像圖景,印證了李明奇工業風酒吧的經營初心,也讓他紮根現實、兼顧理想與溫情的入世特質愈發鮮明。
文學質感融入電影表達:浪漫情懷的現實書寫
《飛行家》本是雙雪濤的短篇小說,相較於其他改編自雙雪濤作品的電影,這部影片雖在情節架構上做了大幅擴容與改編,卻精準表達了原著的文學精神內核。
這離不開雙雪濤的深度參與:他不僅擔綱改編編劇,還以監製身份全程介入創作,文學文本的浪漫底色與現實關照,在銀幕上完成了轉譯。
文學家深度參與電影創作,素來是影響影片藝術風格的重要變量之一,文學的思辨力與表達力,藏在剋制的敘事裏,不刻意煽情,也不渲染滄桑,只以溫潤筆觸鋪陳日常詩意。
喜劇的底色同樣透着剋制。唐僧師徒的戲仿橋段、下落後意外現身的兩瓶酒、隨風飄落的佐羅標牌,這些笑點從不是刻意堆砌的包袱,卻在不經意間迸發蓬勃的生活趣味。

愛情與親情的描摹,亦剝離了煽情的外衣。料理完岳父的後事,李明奇在酒吧中按慣性脫口而出的是 “我得回家給爸做飯了”;小峯坐在父親駕駛的車裏,身體不適時,下意識呼喚的卻是後座的姑父李明奇。這些生活化臺詞,沒有過於戲劇化的悲喜,但表達出真切的人與人之間的溫情。
故事的轉折點帶着強烈的戲劇性的同時亦伴隨溫情平和的主線敘事。
三段式的劇作結構裏,妻弟意外受傷致殘是首個敘事拐點,悄然改寫了主角的人生軌跡;待其從北京歸來,竟夥同友人騙走酒吧,則構成了劇情的第二次波瀾,讓平淡的生活陡生波折。
而當主角最後爲了救治外甥縱身飛向天際時,鏡頭和開頭的飛行呼應,再一次以蒙太奇的剪輯手法將人物的過往心緒與當下飛翔姿態嵌合,讓浪漫的想象與現實質感達成合奏。
結尾2026年老齡階段的片段不長,但恰如片尾毛不易歌聲裏的那句歌詞:“你靜坐在那裏,像一束灌木”,平靜而美好。
回溯影史,文學的 “內向性” 敘事引入銀幕曾突破了商業類型片的敘事桎梏,不僅拓展了電影的表意維度,更讓電影得以掙脫娛樂屬性的單一束縛,成爲承載哲學思辨與文學質感的藝術載體。
諸如雙雪濤等當代文學的書寫者,正在改寫當下中國銀幕的敘事版圖:無論是極具辨識度的 “東北敘事”,還是更廣闊的現實題材書寫,都因文學家的介入而煥發新的生機。
《飛行家》正是這樣一部作品,它在某種程度上跳脫出傳統中國商業類型片的框架,放棄了“地域衰落”與“個體失意”在東北電影中的互喻式表達,用一種近乎超現實主義的方式傳達了一種當下精神,將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在影像上的結合,蛻變爲兼具文學氣質、地域風格與作者表達的獨特銀幕文本,讓文學的浪漫情懷,在現實的土壤裏生根發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