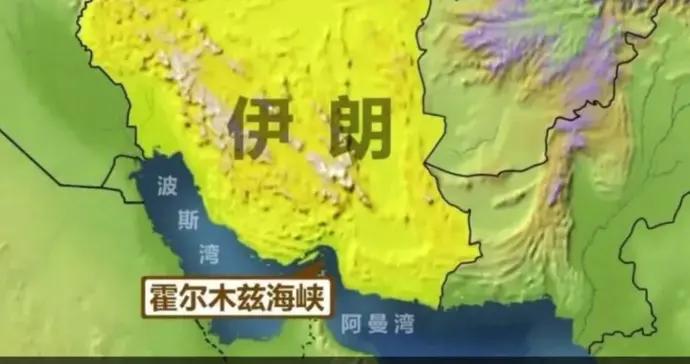隔壁小中長大了 | 小谷




春天、小馬和我 (綜合材料)張燕真
從前小中住我家隔壁。我家從棚戶區搬到井岡山路上那棟“伍單元”的房子是在1974年,我兩歲,我們在那裏住到1982年。從我記事起,就有個小中,和他的妹妹小圓,我們天天相處。
小中比小圓大兩歲,小圓又比我大兩歲。小圓很胖,像她媽,小中很瘦,像他爸。我媽媽說小中是個瘦猴兒,他就笑,小眼睛眯縫起來。
伍單元是那種老式居民樓,一長條走廊連接一層樓的八戶人家,彼此雞犬相聞。我家在三樓,門牌17號,小中家是18號。小中家有兩間房,我家只一間,加一個小廚房,一共15平方。小中家的外間房和廚房的窗戶都朝走廊,加上開着的門,從走廊上走過能清楚地看見他們在屋裏做什麼。小圓媽在廚房做飯,一邊跟小圓爸吵架。我媽媽從公用水池洗菜回來,跟我們說:“小圓的媽一邊吵架,一邊又在偷偷地笑。”小圓爸是個老好人,說話慢條斯理,不會生氣;他在外間屋,也看不見小圓媽在偷笑,只聽見她兇霸霸地吵。
我老記得這個情景:近中午了,小圓和小中拿着煮熟的雞蛋到我家裏來喫,小圓一口一口地啃雞蛋白,啃乾淨了把牙印斑斑的雞蛋黃給小中,再去拿第二個。
“小圓小中,回來喫飯!”小圓媽叫了。
他倆一前一後跑出我們的屋子。從他們家敞開的窗戶能看到他們擺好的桌子,一個鍋裝着幾隻熟雞蛋,還有兩盤本地人頓頓少不了的鹹菜、泡菜。他們家用的碗比我們的大一號。小圓飯量大,跟她哥搶。小圓媽喫飯也是風捲殘雲。小圓爸扒飯夾菜則溫吞退讓,這樣他們的飯桌就出來了錯落熱鬧的節奏。
小圓媽胖,她在走廊上走我們都聽得見:噠噠噠噠,她端着一大腳盆水去公用水池那邊倒了;噠噠噠噠,她又提了一桶水回來了。她不講究地梳了箇中年婦女的髮式:幾根小黑髮卡,左邊右邊地把短髮卡到耳朵後頭去。她一笑,哈哈哈哈。
每逢夏天,小圓媽傍晚做飯前就往走廊的牆上地上灑水。走廊朝南,曬了一天需要降溫,晚飯後家家都把竹椅板凳搬到走廊上來乘涼。一邊搖扇,一邊閒聊,走廊欄杆外有一棵香樟樹,一棵梧桐樹。天黑了,天上星星在閃。有一回,街對面那家單位在頂樓放電影《閃閃的紅星》,我們依稀能看見,也聽得見電影裏的歌聲:“小小竹排江中游……”
一個星期天我爸爸出遠門去釣魚。我和媽媽妹妹在家,妹妹病了,下午媽媽帶她去看病。傍晚了,我一個人不敢呆在屋裏,站在走廊欄杆邊往街上看。他們誰都不回來。天漸漸黑了,別家都點起了燈。我哭起來。小圓媽叫我在她家喫了飯,飯後給我洗澡。她家的澡盆比我們的大,水比我們的燙,她的動作也比媽媽毛糙。她一邊洗一邊數落我:“你哭什麼哭呀!”
那些年,我跟小圓玩得多。跳皮筋,攢糖紙,織毛線,學着編辮子,女孩子玩的各種花樣我們都在玩。跳房子,捉迷藏,打牌下棋,看小人書,那是大家一起玩的,樓裏大小孩子集合起來有一個排。
小中是男孩,有時很調皮。
我們在熊波家看電視。我坐在椅子上,小中坐在牀沿,朝我“啵,啵”地吹唾沫泡。我側身躲,但躲不開,他又不斷地吹。我坐不住,只好走了。他不吹別人,只吹我。是他平時跟我不好嗎?也不是。那他爲什麼要這麼幹呢?沒什麼理由,好像男孩子調皮是正常的,應該的。
有時候,他也跟我兩個人玩,因爲我和他都是獨自在家,沒有其他玩伴了。我們在我家玩捉迷藏。他蒙上眼睛,我藏好,他來找。我幾次都被他找到了。屋裏很小,沒什麼地方藏,我突然找到一個絕妙的地方,竹躺椅上搭着件衣服,我在竹椅前面蹲下,把衣服蓋在頭上,假裝是竹椅的一部分。小中開始找了。“咦,她到哪裏去了呢?”他說,在屋裏打轉,“哎,怪了,到處都不在。”我隔着衣服看他摸到了竹椅旁邊,“嗯,這個是竹椅。我來坐一下。”他坐在了我頭上,我“哎喲”一聲叫起來。
我們到走廊上繼續玩。蒙上眼睛,走廊的牆壁、欄杆,變得難以判斷是哪一段了,空間抽象,步履維艱,全靠摸索。我們玩到了走廊中部樓梯口。小中摸着摸着,突然猛地向後一轉,朝相反的方向撲去。我來不及叫他就踩空,骨碌碌一直滾到樓梯底。那裏放着渣滓盆,邊緣都生鏽磨尖了。他扯下矇眼睛布,抱着膝蓋齜牙。他媽趕來罵他:“看你還摸不摸!”他發狠回嘴:“我要摸!”我後來想着他和他媽的對話笑得打滾,他的神態也定格了下來,一個倔強男孩的側影——他當時大概十歲。
我們家1982年搬走了,是三樓最先搬走的一家,之後其他住戶也陸續搬離。九十年代初,我有一次經過伍單元,還走上樓去看過,樓裏都是不認識的人家了,唯有樓梯牆壁上的斑斑駁駁,和公用水池旁欄杆上的花盆,還宛如昨日。1994年那五棟單元樓拆除,井岡山路也早已改名叫雲集路。
1999年春節,媽媽說想去看看小圓媽,我們就找去了他們家。門緩緩打開,小圓媽站在門裏——頭髮花白,是一個老人了。我說:“韓媽媽,您還認得我不?我是小谷呀!”隔一會,她笑了,讓我們進去。小圓的爸爸左眼白內障,動手術後反而完全看不見了。小中在深圳,小圓已有了小孩子。
2000年春節小中回宜昌,也找到我們家裏。當時我在雲南,他拿手機撥了號,讓媽媽和我講話。媽媽說小中長胖了,特別懂事,很能幹,在深圳做得很發達。她讓他跟我講,我劈頭就說:“你小時候對我不好!”——我那一刻想的是小時候他朝我“啵,啵”吹唾沫趕我走的情景。他愕然,不好意思地說:“是嗎?我都不記得了。”聽聲音我就知道他長胖了,憨憨的。他得知我爸爸在住院,非要送我們五百元錢。
之後若干年還有些來往。2013年我和媽媽在宜昌過年,去了小中新買的房子,他已娶妻,生了兩個女兒,接母親同住。小中說事,就問他媽:“好不好呀?”他媽答:“好呀。”他那些年輾轉多地,在深圳,在東北,在天津,都是做工程。我說起2000年他來看我爸爸的事,他說那一年他覺得自己混得不錯,從東北迴來過年,帶了好多件東北大皮襖,送給他認識的老人們,老人家們都喜眯了:“小中呀——”
那天我拍了些照片,我媽和小中媽的合影,我和小中的合影,小中一家的合影。2016年我媽媽去世,小中在天津,讓他愛人和妹妹來參加喪禮。
我媽媽去世後我家的老屋就荒了。家中堆滿舊物,灰塵積年,入戶水閘也鏽死,出不了一滴水,無法清理打掃。我每年匆忙回來一趟,住酒店,也因爲住酒店,必須匆忙,每次回來兩三天我都是滿打滿算超載運轉地辦事情。其間回一下破敗的老屋,翻翻舊物,發一會兒呆,再鎖上門離開。老屋不能住,我覺得不僅失去了父母的家,也好像失去了宜昌。
光陰荏苒,一年年忙下來:我工作,寫作,做家務,陪讀,女兒上初中、上高中,直到前年高考,步履才稍緩。高考後我們一家回了趟宜昌,在網上找了一家裝修公司,想把老屋整一整。老破小房子整修翻新,這業務也很普遍,來看房的年輕人對老屋的狀況沒有表現出驚訝。他提出一些構想,之後給我發來方案和報價。簡單裝修,預算六萬元,其中第一步是把屋內所有東西都清走,這一項“垃圾清運費”就是一萬多元。房子不清空,工程就不能啓動,但直接把我屋裏的東西視爲垃圾,還要我付一萬多元來清走它們,這比較傷感情,我父母會對此作何感想?屋裏的東西就是他們一輩子的家當,他們一輩子也沒有攢到一萬元。
所以,做不了。我想到小中,給他打了個電話,問他多年做的是什麼工程,跟裝修有無關係。他說他做市政工程,但是他們工程隊的工人也會做裝修。他隨即就有安排,說我回宜昌三趟就可以了:第一趟,把老屋的東西清一清,哪些不要,哪些要留,他找個相熟的三輪師傅來搬,搬運費比較便宜,不要的東西就直接送給師傅;第二趟,裝修隊來家商量方案,我再去採購一批瓷磚潔具之類的材料;第三趟,快完工之前我再回來買必要的電器,並看裝修情況。他在電話裏隨口就部署好了,但我還沒有下定決心。
兩年後的今年,我想好了。今年夏天小中的女兒高考,我去問情況,分數出來填志願,我讓我先生幫忙參謀,他們也恰有此意。高考志願不好填,高價請專業諮詢都未必到位,我先生倒是個好人選。他非常認真,先指導他們填出第一版志願發給他,他對所填的每一個學校和專業都去詳細瞭解,分析考慮所有可能的情形,與他們連線通話後再修改。先後填了四版志願,幾次通話長談,最終定稿,如願錄到了令他們滿意的大學和專業。
填志願之前,小中問我:“你前年說想把老屋整一下?”他一直記着這事。我先不談,等錄取通知書到了之後我才說起。於是,夏天的暑熱快到末端的時候,我回了趟宜昌。
我中午到,下午小中開車來酒店接我,同時約了一個施工隊長和一位三輪師傅來老屋碰頭,看房說事。大致規劃施工內容,說好三輪師傅次日一早帶人來搬運東西,我只有幾個小時來把老屋裏的東西過一遍,決定哪些留,哪些扔,哪些送。
次日,我以爲清理搬運至少需要一整天,然而四位師傅兩個小時就搬完了。清得如此之快,之後我心裏需要很長的時間去跌宕、消化,但當時顧不上。斷舍離是痛的,我不斷告訴自己,時間太倉促,我一瞬間過眼的決定不可能全部是對的,扔的就扔了,留的就留了,不要糾結後悔。家中舊物積存了幾十年,我因爲不捨又留了它們十年,這十年裏對它們莫可奈何,而老屋荒棄也是浪費。不破不立,有舍有得。
然後,施工隊長確定工人,談酬勞,籤合同,買保險,付定金。
我還有一天時間,小中讓我去建材市場把要換的幾扇門窗找好一家店來做,上門量尺寸,再拆舊門窗。他如常上班,那兩天他家中偏有親戚去世,他上午去弔唁,中午來老屋接我去喫飯,邊開車邊語音跟相熟店家點好菜,到店時菜已上桌,我們對坐喫飯,他再送我到建材市場。路上,他跟我講他早些年怎樣跟着老闆走南闖北,他自己怎樣努力考大專、專升本,學土木工程,考二級建造師、考一級建造師……到了某地,他指給我看,前面就是他建的大橋。
我回武漢,老屋開工。每天,施工隊在老屋忙活,我和小中在微信羣裏線上參與。裝修是樁麻煩事,每天都有很多各種事情,一刻也不消停。小中每天下班後都到老屋去看看,每個環節他都跟進,每個細節他都操心。
小中去幫我採購水電材料、瓷磚、潔具、燈具。我別的都不懂,只對瓷磚感興趣,假如我自己去選,只怕要選一天,但我不能太麻煩小中,他進第一家店,我就看中了兩個花色的瓷磚備選,再進第二家店,一比較我就主意定了,就要剛纔那兩個花色,一個鋪房間,一個鋪陽臺。我的直覺很準確,瓷磚鋪出來的效果是一種懷舊的感覺,跟屋裏的老傢俱非常協調。
老屋整修的難點是我想保留舊傢俱。屋裏東西是清理掉了大半,但舊傢俱和一些物品還留着,所以需要騰挪,先把一間房的傢俱全部挪到另一間房,牀拆掉,東西壘疊。這間房整好了,再把傢俱東西挪過來,整那間房。按部就班,到了該挪的時候我就請三輪師傅來挪,付他費用,畫圖告訴他怎麼擺。如此,方得保留老傢俱,既留住了我的念想,又達到了我理想中的整舊如舊,我就是想要一個七八十年代風格的家,我小時候的家。
老傢俱都留下來了——五屜櫃,大約是1979年買的,媽媽終於攢夠了錢,我們在伍單元斜對面的一個傢俱店買下了它,用板車推回來搬上樓。穿衣櫃大約是1980年在同一家店買的。有了這兩個櫃子,我們家多年裝衣服、裝棉絮的紙箱終於扔掉了。這一高一矮兩個櫃子,小中從前都很熟悉。還有七十年代中我媽媽買的別人家的舊牀,這次整修過程中拆開再拼起,也是小中的老相識。1984年請木匠來家打的電視櫃,和七八十年代陸續買的幾把老式靠背椅,清洗打理之後,煥發神采,像傳家的寶貝。
我再回宜昌時,老屋已基本整修完畢,我付清了給施工隊的酬金和工程款。小中來老屋,我讓他站在五屜櫃、穿衣櫃前給他照相,這些櫃子,都認得他呀。
“小中,真感謝你,你幫了我這麼大的忙。沒有你,這件事根本幹不成。”
“沒什麼,這對我來說是小事一樁。”——從某個意義上講,是的,他這些年做了多少大工程,我們老屋整修只算一樁小事,但對我來說就太大也太難。關鍵是,他肯幫這個忙。
我的朋友們的反應:
“啊,他幫你裝修?是你們傢什麼樣的熟人哪,肯幫這樣的忙!”
“而且,怎麼會恰好有這樣一個人,能幫你這個忙呢?”
是啊,怎麼恰好有一個小中,既會辦這件事,又肯幫這個忙呢?而且從我們兩家的關係和小中的處世風格上說,也再合適不過。假如我媽媽知道,是小中幫我們整修的老屋,該多高興啊!我被這個想法感動得幾乎哭了。
我要回武漢了,小中說送我去火車站,我說還有點時間,我去廣場上轉轉,今天週末,古玩舊貨攤點都擺出來了。小中說起有一年他碰到我媽在廣場上擺攤。我爸爸2000年去世,留下了一盒子舊手錶。他是鐘錶匠,幾十年裏積存了一些別人不要的舊錶,他都修好了留着。最後幾年,他把這些表的牌子、年份、來歷都寫在本子上,交代給我,他的意思是這些表將來會是古董,但我當時渾不在意。他走了,我媽媽當然也不懂,她在廣場上擺攤,把這些錶慢慢都賣了,二十元一個,一般都是民工買去將就用。小中說,那天他在廣場碰到我媽在擺攤賣舊錶,他就買了一個,現在那個表還在。
2025,11,27-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