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家與期刊主編探討:當下長篇小說的地域書寫有哪些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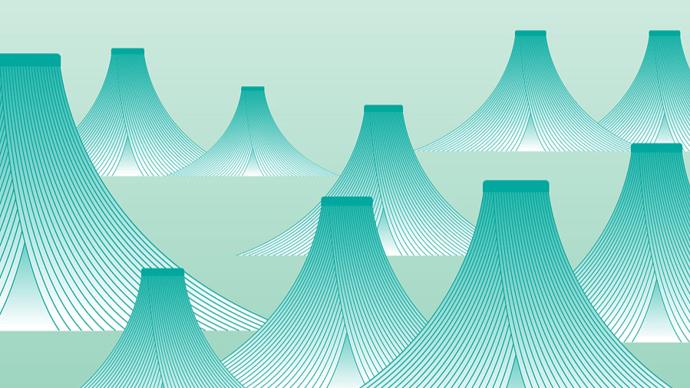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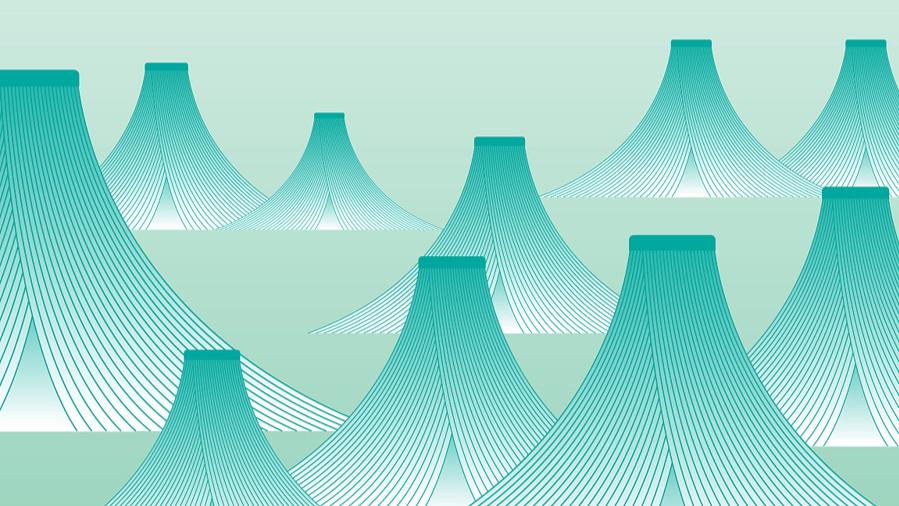
當代長篇小說創作,亟須對新時代社會生活、文化結構、科技創新、傳播格局等一系列深刻變化作出積極回應。身處數智化浪潮,長篇小說的地域書寫不再僅是故事展開的背景板,而是作爲一種根本性的敘事方法與架構,將“地方性知識”淬鍊爲具有普遍意義的“中國故事”,深度參與到對中國現代性經驗的詮釋之中。在近期舉辦的第二屆長篇小說錢塘江論壇上,來自全國各高校、魯迅文學院、文學期刊的專家、學者及文學研究者,圍繞地域書寫的本質價值、實踐形態、現實困境等關鍵問題展開研討,爲新時代長篇小說創作與研究的深化提供思想資源。
——編者
地域書寫更是一個流動的跨界概念
吳義勤(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副主席):作爲文學的重要體裁之一,長篇小說承載着時代的精神氣息,具備描繪現實、建構歷史、發展敘事的獨特能力。長篇小說也是檢驗一個國家文學創作實力的重要標誌,對文化傳承、閱讀引領與審美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來,我國長篇小說繼續保持旺盛的創造力。“50後”“60後”作家持續推出重要作品,“70後”作家展現出穩定的創作實力,“80後”“90後”作家則不斷以嶄新的表達方式參與文學現場,網絡文學作家也在拓展敘事邊界、豐富文學表達。多代作家在同一文學場域中相互映照、彼此激勵,形成了活力充沛、格局多元的創作景觀。他們的作品既關注新時代中國社會的深刻變革,也體現對傳統文化的再闡釋;既觸及城鄉現實,也深入人的精神世界,對時代、歷史、命運、人性進行持續而深刻的思考。
長篇小說記錄廣闊時代,深入挖掘人性,其漫長的創作過程是對作家功力和毅力的試金石,也是衡量一個國家文學水準的核心標尺。作爲檢驗國家文學實力的核心載體,長篇小說近年來呈現多代作家同臺發力、題材多元拓展的繁榮態勢,但創作短板與研究盲區仍需正視,亟需從四重維度深化推進。
一是要加大對新時代長篇小說特別是“兩個計劃”長篇小說入選作品的研究,克服對主旋律、主題創作和現實題材創作的誤解,切實對長篇小說面臨的藝術問題進行研究;二是要加強長篇小說文體及理論思潮研究,對歷史虛無主義等在小說中的表現有專業的辨析;三是對長篇小說的藝術經驗進行及時總結,爲當代文學的歷史化、經典化作貢獻;四是對網絡文學等新的藝術可能性進行敏銳跟蹤。新時代長篇小說的發展,既需要創作層面的精品意識,更依賴研究層面的學理支撐。唯有聚焦核心問題、深化學術探索,才能推動當代文學在高質量發展道路上穩步前行,爲文化強國建設注入文學力量。
郭豔(魯迅文學院副院長):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長篇小說創作呈現出一個深刻的變化:地域性不再僅僅是故事發生的背景或點綴,而是逐漸演變爲一種核心的敘事方法與意義生成的機制。這一轉變超越了早期“尋根文學”的範式。在全球與後全球化的語境中,地域書寫已成爲中國作家理解、詮釋並批判性反思現代性經驗的重要路徑。近三十年的關鍵進展在於,地域從被描述、被觀看的“對象”,轉向了主動參與建構意義的“主體”。這既體現爲作家的創作自覺——如在莫言、賈平凹等作家的筆下,故鄉不再是簡單的回憶對象,而是在全球化浪潮中抵禦文化同質化、思考民族身份的精神根據地;也體現爲書寫深度的掘進——地域不再侷限於獨特的風俗景觀,更深入到特定空間所孕育的認知方式、情感結構與世界觀。通過對不同地域應對現代性衝擊的差異化經驗的呈現,中國作家貢獻了具有獨特價值的中國故事與中國經驗。
具體而言,東北與江南的敘事,代表了兩種風格迥異的美學體系。東北敘事根植於其厚重的工業歷史與轉型陣痛,文本結構常呈現出如工業廢墟般的斷裂感與拼貼性,這本身即是對線性歷史進程的隱喻性質疑。相比之下,江南敘事則承襲了千年文人傳統與市井商業文明,發展出一種精緻、內斂、富於思辨的美學。然而,這兩種成熟的敘事模式也面臨着各自的困境與挑戰。東北敘事存在“內卷化”的風險,工廠廢墟、下崗創傷等高度符號化的主題易陷入悲情主義的自我重複。江南敘事則可能因對細節與韻味的極致追求而陷入“精緻的繭房”,在精雕細琢中鈍化了把握更粗糲、劇烈社會變革的能力,並有以美學化敘述消解歷史內在衝突張力的傾向。此外,地域特色在傳播中易被簡化爲可消費的文化符號,從而削弱其思想的深刻性與批判性,這也是需要警惕的普遍問題。
展望未來,地域書寫或許可以在以下方向進一步深化:一是挖掘地域的哲學維度,使其不僅作爲故事場景,更能成爲獨特認知框架與價值觀念的來源,爲反思現代性根本問題提供思想資源;二是強化其內在的批判性,避免沉溺於風情展示或文化鄉愁,保持對地域內部複雜矛盾與權力結構的敏銳洞察;三是在地方性與全球性之間建立對話,自覺將中國的地域經驗置於全球現代性的視野中考察,使其成爲世界文學圖景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哲貴(《江南》雜誌主編):地域書寫在當代文學創作中呈現出豐富而複雜的多元樣態。第一種如作家葉兆言,是在地書寫的典型代表。他長期生活於南京,創作幾乎未曾離開這座城市,其作品深度參與了南京文學形象的構建,使其自身也成爲這座城市的一個文化符號。這是一種作者與地域深度綁定、同步生長的創作模式。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包括我在內的離鄉書寫路徑,作家們已離開最初的生長地,定居於新的城市,然而核心的書寫對象,卻依然錨定在曾經的故鄉。這些都清晰地表明:物理空間的遷徙並未割斷創作的精神臍帶。故鄉作爲經驗源頭與情感原鄉,在離開後反而可能獲得更強烈的審美觀照與更集中的藝術提煉。
地域書寫還觸及第三種更爲特殊的模式,不妨稱之爲精神原鄉的書寫或情感投射式書寫。以河南籍、長期生活於北京的作家柳建偉所創作的《錢塘兩岸》爲例,這部以80年前抗戰時期浙江爲背景的小說,從籍貫與常居地看,似乎與作者缺乏直接的地緣關聯。然而,深入地瞭解揭示了其創作的深層動因:長達20年的資料準備與頻繁赴杭考察,展現了驚人的功課深度。對於柳建偉而言,浙江並非血緣故鄉,卻通過長期的情感投入、歷史調研與細節體認,昇華爲一個概念上的、情感認同的故鄉。這表明,地域書寫的疆域可以超越出生地與現居地的物理限制,指向一個由研究、想象與深情共同構建的精神空間。這三種路徑共同豐富了地域書寫的內涵,證明其核心並非簡單的地理標識,而是關聯着身份認同、情感歸屬、歷史思考與藝術創造的複雜實踐。

劉永春(揚州大學教授):在我看來,地域書寫的核心並非單純書寫地域本身,而是以地域爲視角、以地域身份觀照並書寫快速發展的中國歷史、現實與未來。但我的思考過程中始終存在兩個核心困惑。
其一,經典地域書寫如魯鎮,能夠以地域鏡像折射整個世界,但在現代尤其是當代多數地域書寫中,卻難以實現這種超越性——多數作品僅能呈現等同於或小於地域本身的視野,這一判斷或需進一步商榷。其二,當前地域書寫易自動與鄉土書寫綁定,但對當下及未來中國文學而言,更亟待解決的命題是“城市作爲地域如何表現”。事實上,當作家對自身生活或童年記憶中的地域形成對照鏡像時,地域書寫才能進入更深層次。而以城市視角反思鄉村或以鄉村視角反思城市,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地域書寫的常見模式。
若想讓地域書寫如魯鎮、馬孔多般產生普遍意義,或以地域視角觀照更廣闊時間維度中的中國,就需明確:地域書寫是構建當下中國敘事的重要組成。當下中國的文學呈現,取決於我們對地域書寫的認知深度。因此,我更傾向於將地域視爲動詞、形容詞,而非單向的名詞。
謝尚發(上海大學副教授):當前地域書寫存在不夠深刻的突出問題。多數創作停留在對地方本身的表層強調,卻未深入追問地方究竟是什麼以及地方如何影響長篇小說創作,地方能否提供真正的思想資源。在大批量長篇小說生產的市場背景下,這種表層強調實則是作家的焦慮外化:通過貼上“新南方寫作”等標籤凸顯自身,實現傳播與交流,卻鮮少從文學延伸至文化地理學、人類學、社會學等領域,探究地方如何規定人的深層邏輯。人文地理學中的在地人文主義流派早已深入探討此類議題,文學創作完全可以汲取這些學科資源,以形象化表達挖掘地方對人的深層規訓。正如學者貝爾唐·威斯特法爾在地理批評中所言,文學常走在理論前端,人文地理學需向文學借鑑資源與思想——若能實現這種跨學科融合,長篇小說的地域書寫便能抵達更深刻的哲理與思想層面,規避同質化困境。
當前地域書寫本質上是從總體到細分的過程。小說的核心使命是表現人性與世間普遍道理,而地域則是實現這一使命的具體錨點,由此衍生出“新東北寫作”“新南方寫作”“文學新浙派”“新皖軍”“蘇軍”等細分概念。這些創作雖取材與人物形象各具特色,但最終都指向總體性命題。正如清代理學家李光地所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無論地域多麼獨特,其承載的思想內核終究離不開普遍人性的共通之處。地方如何塑造個體恰恰是長篇小說地域書寫的突破切口,卻常被作家忽視。總體而言,地域書寫中局部與整體、普遍人性思想與獨特地域取材之間並非割裂對立,而是存在內在溝通。
長篇寫作生態的挑戰與拓展
翟業軍(浙江大學教授):每種文體都是有生命的,有生長也有消亡。長篇小說的興起,源於人們對異己新奇經驗的需求,正如本雅明所言“遠行的人必有故事”,我們通過聽故事獲取經驗。但在媒介翻新、信息爆炸的當下,在短視頻主導的時代裏,長篇小說的創作與閱讀都需要大量時間和精力,讀者需投入數日沉浸陌生世界,這顯得“匪夷所思”。因此,長篇小說雖未消亡,卻面臨巨大挑戰,必須重新思考自身的存在意義與可能性。
長篇小說創作者是用身體感知世界,而非單純用眼睛,他們要捕捉不可感知的內核,以隱喻呈現基座性現實,這種綿長的感知積累天然呼喚長篇體裁。長篇小說從不“傷口撒鹽”,它描述傷口形狀、揭示創傷成因,本質是爲時代做精準的精神分析。直面當下時代精神狀況,我們依然需要長篇小說這一文體。
張鵬禹(《人民日報》海外版編輯):當下長篇小說創作面臨一個突出問題:鮮有破圈並受到社會公衆廣泛關注的作品,如今多數長篇小說正遭遇讀者匱乏的危機。回望歷史,莫言在《捍衛長篇小說的尊嚴》中曾指出,長度、密度與難度是長篇小說的標誌與尊嚴,他認爲“長不是影響優秀讀者的根本原因,好纔是長的前提”。時隔近二十年,這一觀點依然成立,但時代語境已發生深刻變化。
當下時代語境主要呈現兩大特點。其一,我們進入了全球化的加速社會,碎片化生活切割了人們的時間,導致注意力分散。學者羅伯特·哈桑在《注意力分散時代》中提到,啓蒙經典被數字信息遮蔽,慢性注意力分散讓穩定思想愈發難得,雖需經典卻難再構建經典。其二,人工智能與時代深度融合,外交家基辛格在《人工智能時代與人類價值》中警示,人類知識狀況正經歷“麥哲倫式革命”,人工智能或終結人類理性主導的世界。如今很多人依賴AI篩選、組織信息認識世界,而非通過具身體驗,且算法黑箱問題讓人類難以理解AI的認知生成過程。
核心問題隨之而來:我們能否回應時代語境,催生新的長篇小說樣態?回望歷史,文學史家瓦特在《小說的興起》中指出,18世紀英國現代小說的興起,與個人主義興起、資本主義發展及中產讀者出現密切相關,是呼應現代性的文化工具。當下媒介發展始終與文學樣式變革緊密相連,網絡文學、短視頻的興起均與技術發展同步,長篇小說創作需主動回應時代。值得關注的是,《煙霞裏》《平樂縣誌》《鄉野新風四重奏》等作品已開始嘗試文體變革,如借鑑紀傳體、模仿傳統志書、雜糅書信等文體,這種變革或與碎片化生活語境相呼應,值得深入研究。當下長篇小說的文體變革,能否催生類似18世紀英國現代小說的全新文學題材,這考驗着作家與批評家的眼光和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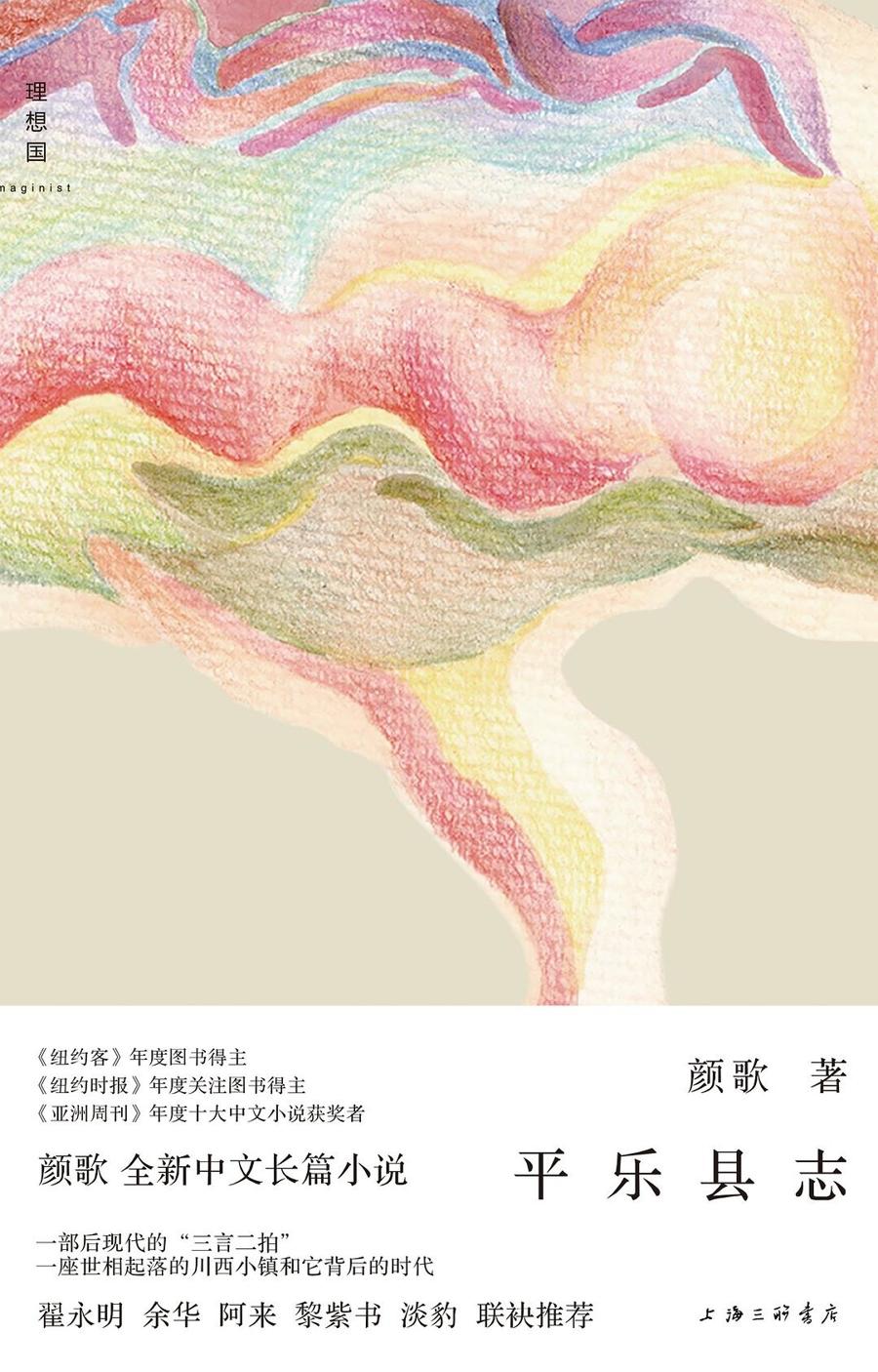
張永祿(上海大學教授):關於長篇小說如何發展,我結合創意寫作的實踐與觀察,提出三個方向性的構想:
其一,倡導“慢寫作”,重拾經典的深度與智慧。高質量發展,理應以傳統經典爲重要參照。經典作家往往以數年甚至數十年心血熔鑄一部作品。反觀當下,鍵盤寫作極大地提升了書寫速度,部分作家乃至網絡寫作者日更數千字、年出一部長篇已成爲常態。然而,寫作並非比拼“手速”。許多高速產出的作品質量平平,甚至不及作者早期精心打磨之作。長篇小說不僅是技術活,更需要深厚的生活積累與生命智慧的綻放。遺憾的是,不少作品僅停留在輸送庸常識見或情節消費的層面,未能提供獨特的精神啓示、情感共鳴或批判性思考,其價值甚至難以與深度新聞報道或優質短視頻內容競爭。因此,當代作家有必要“寫慢一點”,迴歸對生活的沉潛體驗與對人生的深刻洞察,這是向經典致敬的必經之途。
其二,期待“兼職寫作”成爲高質量作品的新興源泉。在人工智能輔助寫作日益普及的“大衆寫作時代”,純靠寫作謀生的“專業作家”比例可能減少,而擁有其他職業背景、基於豐富人生經驗進行書寫的“兼職作家”將越來越多。當千行百業的人們投入小說創作,他們所帶來的獨特行業經驗、人生故事與生命感悟,很可能爲文學注入前所未有的新鮮血液與深厚智慧。這些來自更廣闊生活領域的書寫,或許比侷限於單一文學圈層的創作更值得期待。
其三,拓展長篇小說的社會文化功能。長篇小說在保留精神探索價值的同時,應強化其形而下的、與社會實踐結合的文化功能。如小說可以更積極地與文化經濟、公共文化建設相結合。未來,長篇小說或許應更注重其作爲文化產品、作爲文明交流與對話載體的功能,這可能是其在新時代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機遇。
地方性也包含着中國與世界
吳玄(《西湖》雜誌主編):語言與文體存在天然關聯,這種對語言的極致追求,決定了浙江作家更適配中等篇幅的創作,而在長篇小說創作上則面臨天然挑戰。以浙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魯迅爲例,其創作重心亦集中於中短篇領域,並未涉足長篇小說,這與他對語言精準度的極致把控密不可分。即便未來語言的重要性可能有所弱化,使得長篇創作成爲可能,但在我看來,一部魯迅式的短篇小說,其價值遠勝於千萬字的冗長文本。對浙江作家而言,堅守語言追求仍是值得肯定的創作立場,但若要兼顧這種追求與長篇小說創作,其間的矛盾亟待解決——這一困境唯有創作者自身能夠感知,外人難以提供直接解決方案。
地域書寫的核心,並非糾結於對故鄉的虛構或寫實,而在於釐清寫作者與地域之間的關係維度,尤其是二者的距離感。若以古典主義創作視角觀之,寫作者與地域可能處於“零距離”狀態,作品中充盈着優美的鄉愁意涵——正如現代文學時期沈從文的創作,湘西對他而言既是故鄉,亦是承載理想的烏托邦。而進入現代主義創作語境,寫作者與故鄉的關係則發生根本轉變:對原生故鄉的陌生感成爲核心體驗,這種遙遠的距離感催生了獨特的創作形態。正如作家加繆所言,當個體對原本熟知的故鄉產生突然的陌生感,荒謬感便隨之產生,而這正是現代主義寫作的重要源頭。
海飛(《浙江作家》主編):作爲長期創作長篇小說的寫作者,我的思考源於實踐經驗而非理論推演。我始終在探尋一個核心問題:爲何東北年輕一代作家的創作個性格外鮮明,而南方年輕一代作家的個性標識卻相對模糊?這是客觀存在的創作現象——無論依託何種創作概念或表達路徑,南方作家羣體始終未形成類似東北作家的鮮明特質,其背後成因值得深究。
與此相關,我也在反思“縣城寫作”的核心內涵。縣城寫作絕非簡單復刻縣城生態,這一概念已引發諸多小說創作與評論探討。我曾讀過一部幾十萬字的抗戰題材作品,書中每個章節標題均爲城市名稱,城市空間隨情節推進不斷切換,形成典型的城市書寫特徵。這讓我聯想到自身創作:我出身農村,早期多聚焦農村題材,但如今的農村書寫存在明顯斷層——要麼農村題材創作式微,要麼仍停留在30年前的農村敘事,鮮活的當代農村圖景在創作中近乎缺失。
轉向城市書寫後,我有過諜戰小說創作經歷,曾書寫南京、寧波等多個城市,但事後反思發現,這類城市書寫多流於表面,未能真正觸及城市的精神內核。我常與同行及年輕作者交流創作心得:無論書寫人性還是其他主題,核心應聚焦人與人的關係,構思情節時不必過度堆砌,而要深入挖掘人物的內心訴求,這種創作思路已被驗證有效。比如影視劇《漫長的季節》,其敘事內核貼合縣城寫作範疇,若用文學語言轉化重構,必然是一部精彩的文學作品。這引發我進一步思考:文學語言與強大故事內核的結合,是否能讓小說更具感染力?南方創作未必只能侷限於細膩溫婉的風格,強勁的故事張力或許能爲小說開闢新路徑。
夏烈(杭州師範大學教授):以我較爲熟悉的網絡小說領域爲例,其長篇創作與地域書寫的關係一直處於動態演變之中。早期網絡文學(如安妮寶貝、慕容雪村的作品)雖常聚焦於北京、上海、成都等具體城市,但其內核並非簡單的地方風情展示,而是藉助地理座標抒寫一代青年的普遍心理與現實批判。互聯網賦予的“數字位置”使其呈現出去中心化、平民化與高度自由的特質。這一格局在2015年前後發生顯著變化。隨着主流社會對網絡文學創作提出“關注現實題材”的引導,許多網絡作家開始主動對接地域與重大現實命題。如何常在的《浩蕩》等作品,即“正面強攻”式的創作,標誌着網絡作家從彌散狀態向某種“再中心化”的奔赴,其優秀成果也有機會進入傳統主流文學視野。
此外,網絡文學還催生了地域書寫的另一種創新路徑。一些作品並未刻意突出地域性,卻意外成就了鮮明的地域IP,並帶來文化紅利。例如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的科幻小說《我們生活在南京》,其核心是未來敘事與時空穿越,卻成功將“南京”這座城市塑造爲極具標識性的故事空間。同理,馬伯庸的《長安十二時辰》等作品,也以歷史傳奇激活了古都的地域魅力。這揭示了科幻、歷史等類型小說與地域文化結合的巨大潛能,爲地域IP的創造開闢了新場域。
縱觀網絡長篇二十餘年的發展,地域始終是其書寫的重要維度,但其內涵與功能持續更迭,呈現出在去中心化與再中心化、自由表達與主流引導、彌散與聚焦之間不斷刷新、糾纏的辯證關係。這爲所有創作者提供了多元參照:既可以堅持個體化的精神位置書寫,亦可主動參與地域現實的主流敘事,關鍵在於找到屬於自己的、有生命力的藝術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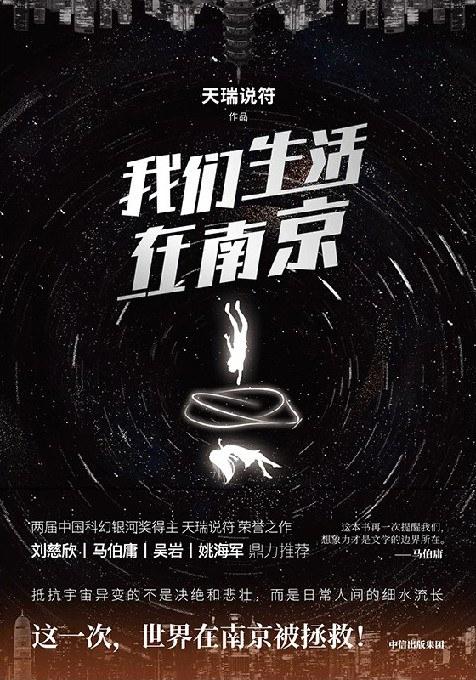
田振華(江蘇師範大學副教授):作爲鄉土文學的研究者,我對“新時代山鄉鉅變創作計劃”已出版的作品進行了系統閱讀。雖然作品質量與可讀性存在差異,但通過整體梳理,我認爲這批創作呈現出三個值得關注的創新面向,同時也暴露出一些亟待突破的深層問題。
三個顯著的創新價值在於:第一,實現了對書寫地域的“再主體化”。不同於過去鄉村書寫中或將鄉村視爲啓蒙客體或進行浪漫化讚美的視角,這批作品嚐試在新的時代語境下,重新確立鄉村及其生活者的主體地位。這與趙樹理時代的“主體化”既有精神延續,又因語境變遷而產生了內涵上的重要區別。第二,體現出強烈的“地域再造”雄心。作品中的鄉村圖景,並非對現實的簡單摹寫,而是融合了實地觀察與文學想象的建構。其中蘊含着作家對“山鄉鉅變”理想圖景的展望,展現了以文學參與鄉村形塑的能動性。第三,呈現出鮮明的“新大衆化”傾向。其敘事風格與審美趣味有意識地向大衆靠攏,呼應了當前“新大衆文藝”的發展潮流。值得注意的是,此創作計劃的提出早於“新大衆文藝”概念的廣泛討論,其大衆化實踐具有一定前瞻性。
然而,這批作品也普遍面臨兩個核心的創作命題:首先,如何處理好地域性與世界性的關係。許多作家投入深厚情感書寫特定地域,但有時難以將個人化的強烈體驗,轉化爲具有普遍共鳴的審美形式與世界性意義的表述。這導致了作者自我感動與讀者感受脫節的風險。
其次,如何平衡大衆化與經典化的可能。大衆化不等於扁平化,諸如《紅樓夢》《三國演義》在其時代亦是大衆讀物,卻因思想與藝術的深度而成爲經典。當前創作在追求可讀性的同時,亟需思考如何在“大衆化”路徑中注入深刻的哲學思考與持久的藝術價值,從而經受住時間的檢驗。這既需要作家的自覺突破,也呼喚批評界建立起與之匹配的有效闡釋話語。
周保欣(海南大學教授):當下討論地域書寫,需關注其流動性新特徵。過去我們多將地方視爲靜止的,如今的新南方文學、新東北文學等概念,既有新舊時間維度的對比,更有重新認知中國空間的意義。以我自身經歷爲例,此前從杭州赴海南任教,最初竟有前往偏遠地區的刻板印象,實則海南是連接湄公河流域國家與東南亞各國的十字路口,當地先民的“更路簿”(記錄出海水文、氣候的文獻)便印證了其早期的海洋性特質。再如新西部文學創作,如今書寫河西走廊、新疆,已擺脫過去中原中心主義的邊陲視角,而是將其視爲連接中國與歐洲、西亞、中亞、印度的中介樞紐。這意味着,當下的地域書寫需要立足“何以中國、何以地方”的立場,重新發現和書寫地方。
我們應摒棄刻舟求劍式的地域理解,尤其反對以行政地域劃分作家(如江蘇作家、浙江作家)。行政區劃不具備充分的文化說服力,以自然地理(山系、水系)劃分更準確,一個地方、一個國家的歷史走向,很大程度上由地理決定,而地理也可在相當程度上解釋文學史與文學現象。比如討論浙江長篇小說高質量發展,不能簡單對比當代與五四時期的作家數量,更應關注浙江的文化氣韻與時代文化氣象的契合度與碰撞點,這纔是理解地域文學發展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