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中國古代法制的三個視角



電視劇《白鹿原》中有這樣一個情節:當黑娃帶着身份不明的田小娥從外地回到原上,希望族長白嘉軒能允許他們以族人及妻子的身份進祠堂拜祭祖先時,不僅白嘉軒沒有同意,連黑娃自己的父親(同時也是白家的長工)鹿三也堅決反對,甚至厲聲責問黑娃:“哪兒來的?搭眼一看就知道不是窮家小戶女子,怎麼會跟你走?三媒六證了嗎?說!給老子說明白!”這句話中的關鍵詞是“三媒六證”——三媒是指男方聘請的媒人、女方聘請的媒人,以及給雙方牽線搭橋的中間媒人;六證是指見證婚姻的六件物品,即在天地桌上擺放一個鬥、一把尺、一杆秤、一把剪子、一面鏡子、一個算盤。在鹿三和白鹿原鄉民的觀念裏,甚至可能是那個時代絕大多數中國人根深蒂固的思維裏,三媒六證是男女雙方締結婚姻的必要條件,是賦予婚姻合法性、正當性的必經程序,否則即爲非法的婚姻,因此白鹿原並不承認他們婚姻的有效性。
歷史沿革的視角
提到“三媒六證”的影視作品還有很多。新近出版的《表象背後:文藝作品中的法律小史》中,作者列舉並解讀了古典文學經典《西遊記》裏“三媒六證”的細節。第19回“雲棧洞悟空收八戒,浮屠山玄奘受心經”中,孫行者調侃豬悟能:“像你強佔人家女子,又沒個三媒六證,又無些茶紅酒禮,該問個真犯斬罪哩!”可見,以“三媒六證”的標準來衡量,豬悟能的婚姻也屬非法、無效,還可能涉及刑事犯罪。作者進一步介紹,早在西周時期,對男女嫁娶已有嚴格要求,“三媒六證”之外,“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也是必須遵循的婚禮程序。其中的納徵就相當於我們今天還在繼續沿用的訂婚習俗,與訂婚環節相關的聘禮或者彩禮也就自然而然成爲無法迴避的話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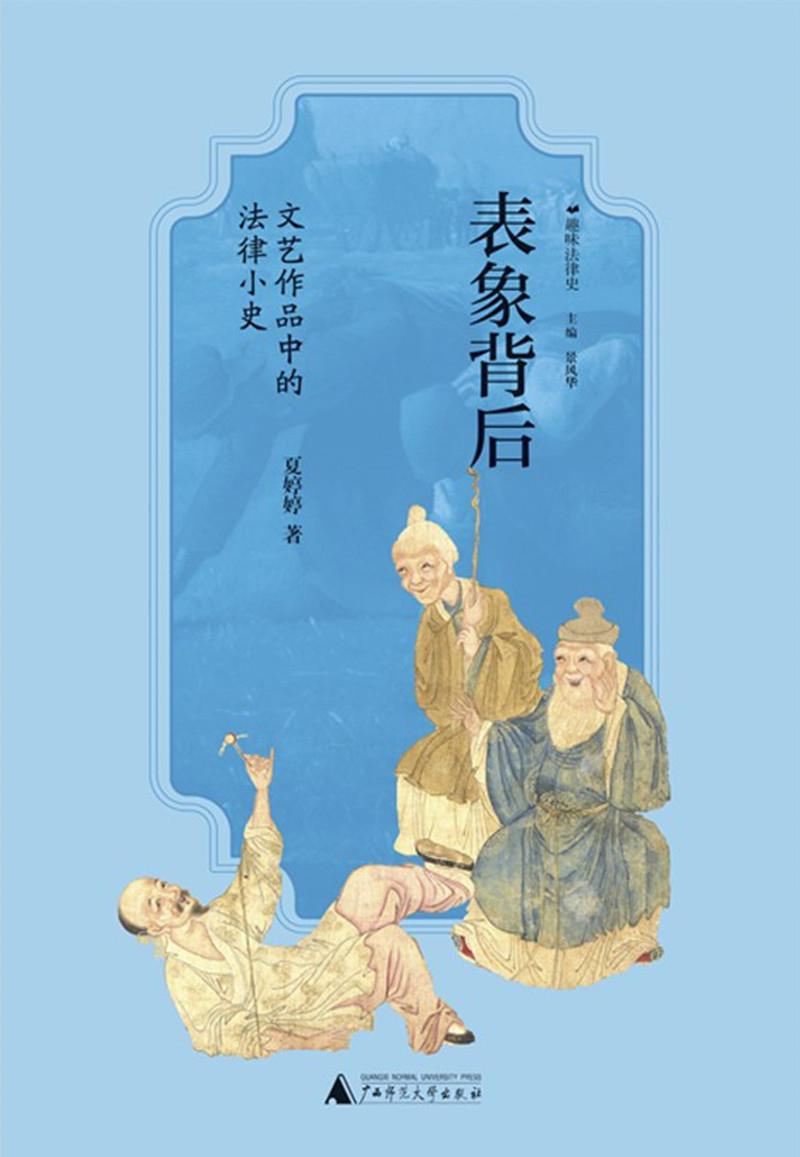
《表象背後:文藝作品中的法律小史》,夏婷婷 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5年出版
網絡上曾有流量文章以省級行政區爲單位,將中國的廣大區域劃分爲高彩禮地區、中彩禮地區、低彩禮或靈活協商地區,還有網友專門製作了全國彩禮地圖。伴隨着每一次與彩禮有關的新聞事件,這些流量素材都會一再地進入公衆視野,並不時引發一些將彩禮定義爲陋習並希望予以取締的呼聲。
然而,如果以自古而今的視角看待中國古代法制,就會發現,彩禮從中國古代的制定法到現在的民間習俗,從古代的必經禮儀程序到現在的因地因人而異,綿延幾千年,可謂源遠流長;儘管其強制性已不復存在,但其生命力仍不可謂不頑強,廣大民間自有其適合生存的土壤,並非簡單地能夠以封建陋習定義之、取締之。因此,在官方出臺的關於彩禮糾紛如何處理的相關文件中,一方面當然是明令禁止借婚姻索取財物,另一方面則是要求考慮當地習俗、家庭經濟情況等多重因素進行綜合評判、分類處理,而非一刀切地以無效了之。某種意義而言,這也是國家法律與民間習俗之間的一種互動和呼應。因此,如果以歷史沿革的視角觀察中國古代法制,我們在認識歷史上或生活中某種制度或規則或習俗的長期性、複雜性、厚重性時也許會多一份敬畏,在尋求變革時則會多一份深思。
辯證法的視角
有關中國古代法制的通俗類作品,由於題材(涉及古代刑案、古代婚姻、宮廷祕聞等)本身頗具吸引力,加上文風的曉暢、風趣、易懂,還經常能帶入一些現代人的視角,產生思維碰撞,使得這類作品在圖書市場上頗爲流行,比如《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國法律史》。這本書圍繞北魏蘭陵長公主和駙馬劉輝的悲劇故事展開,對婚姻、暴力、犯罪、親屬容隱、連坐等中國古代法制的常見論題夾敘夾議地進行了分析梳理,讓讀者能夠較爲近距離地觀察到當時中國的法制風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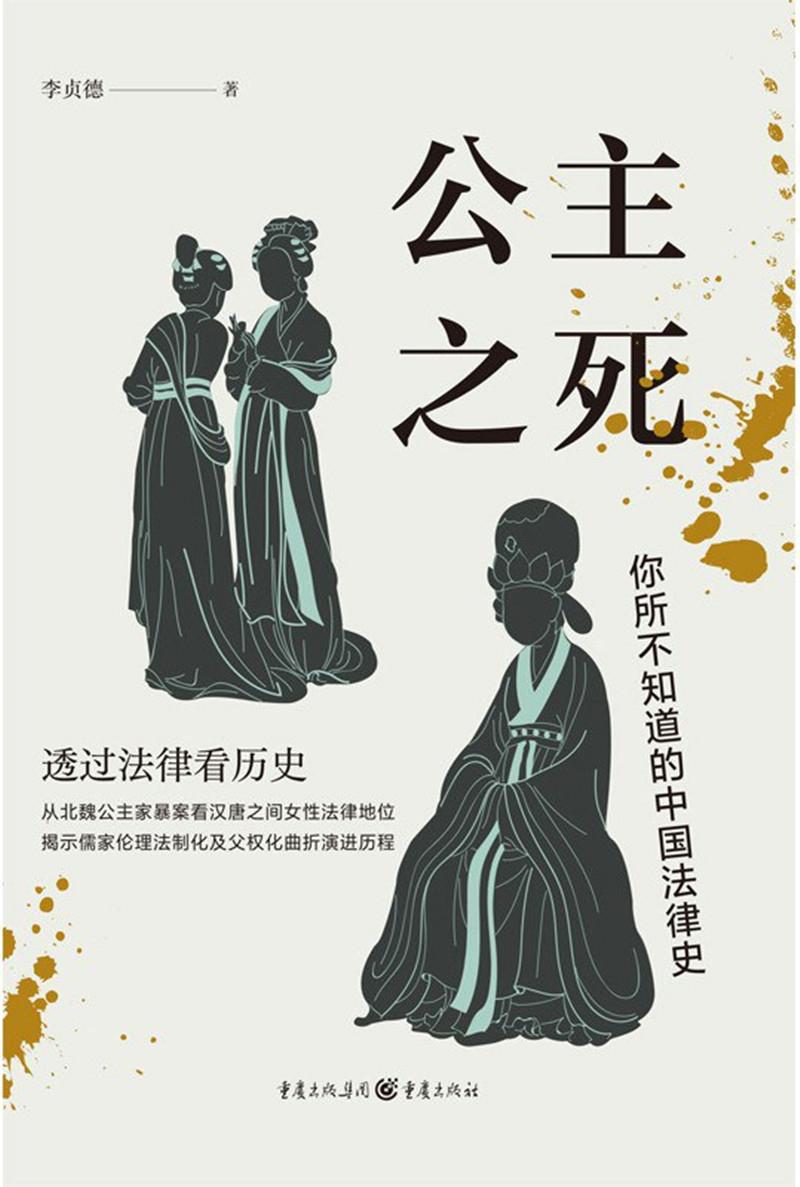
《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國法律史》,李貞德 著,重慶出版社2023年出版
在筆者看來,其中最具啓發意義的是作者引述故事所展現的辯證法視角。作者在書中引述了東晉名相謝安與其夫人劉氏關於納妾一事的不同觀點:謝安的學生援引周公著述來推導出劉氏禁止納妾是因爲她缺少不妒忌的美德,而劉氏不以爲然,反而犀利地指出該問題的根源是在於周公制禮,如果周婆也有制禮作樂的機會,則斷然不會出現這樣的局面。作者提醒大家:歷史上的政治制度、社會規範、倫理價值,以及記載這些標準的敘述書寫,是從誰的視角和位置發出的聲音,作爲讀者是不可不加以考察的。書寫者與閱讀者、正面與背面,都是觀察問題的不同角度,我們暫且可將其歸入辯證法的視角。
古詩有云: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如果以辯證法的視角來觀察中國古代法制,面對同一個問題,可能會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比如以“大義滅親”這一古代法制中的經典論題爲例,現在對該成語的通行解釋是:爲了維護正義,對犯罪的親屬不包庇,使之受到應得的懲處。這顯然已具有褒獎的含義,可是在古代中國,這是一個爭議極大的問題。儒家既鼓勵犯罪者的親屬包庇罪犯,也同樣鼓勵受害者的親屬不經執法部門而手刃大仇。贊成者認爲,大義滅親是以國法爲先,如鐵面無私的包公斬了自己寡嫂的獨生子,其高風亮節傳唱至今。反對者則認爲,殺親是滅絕天倫、泯滅人性的行爲,殺親者不值得信任,尤其從古代統治者的角度,一個滅絕人倫的統治者很可能會給天下帶來更大的災難,倘若純粹以社會公利來作價值計算而不去制約德行有虧的行爲,那麼所謂的社會公利反而會遭受更大程度的損害。因此,最終反映在歷史上,幾乎同類型的行爲,有的被定性爲“大義滅親”,有的卻被界定爲“滅倫背義”。
中西比較的視角
與《表象背後》同屬“趣味法律史”系列叢書的還有《故事正義:文學影視中的法律文化》,該書主要以中國古典小說和熱門影視作品爲研究素材,藉助文學或影視中的故事豐富人們對法律問題的認知。巧合的是,書中一篇《公主爲什麼不幸福?》講述了北宋福康公主的悲劇故事,同樣也遭遇了丈夫不忠和家庭暴力,其人生軌跡與《公主之死》中的蘭陵長公主幾乎如出一轍,在皇權與夫權的鬥爭之下,即使尊貴如公主也無力掌控自己的命運,雖相隔幾百年,確屬實實在在的歷史重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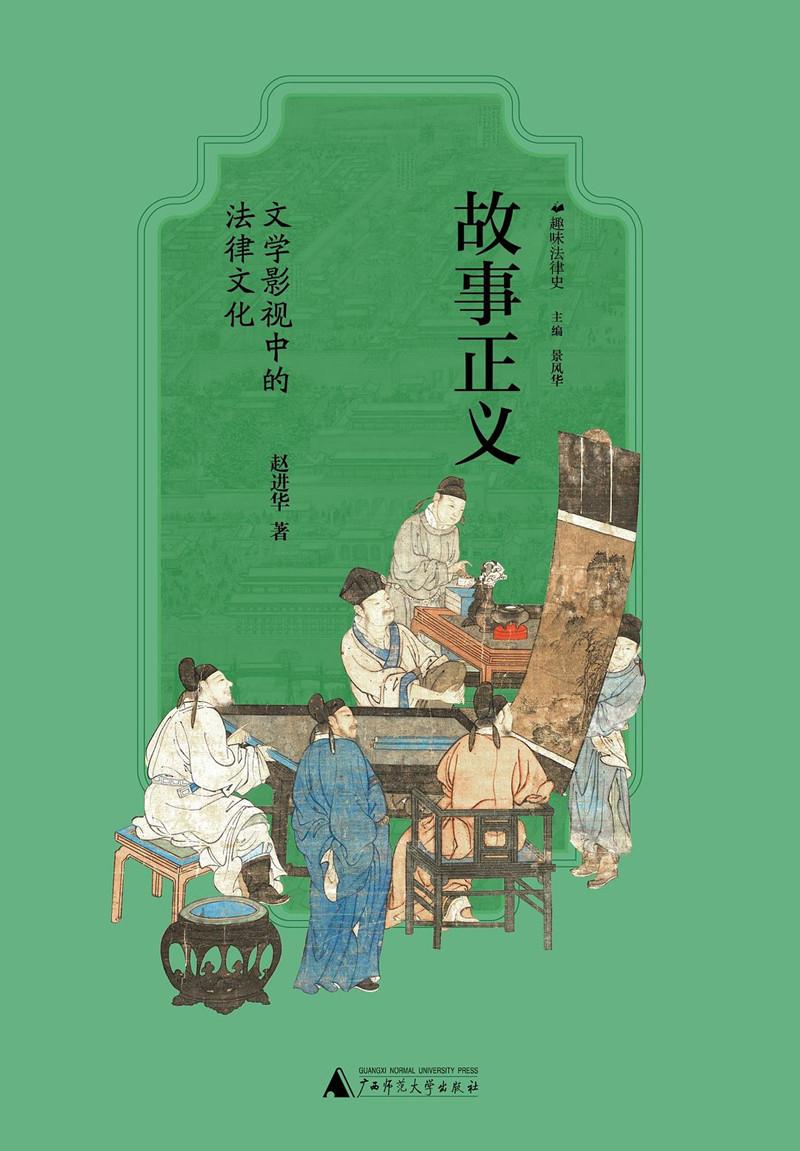
《故事正義:文學影視中的法律文化》,趙進華 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5年出版
縱觀三本著作,《公主之死》是以北魏蘭陵長公主被駙馬毆打流產致死引發刑案作爲切入口,討論了官僚集團與皇權在確定涉案人員罪名及刑罰輕重方面的共識和分歧,以及漢唐之間幾百年裏女性的法律地位、司法傳承情況等,屬於比較典型的“小題大做”,較爲適合具有一定法律基礎知識的讀者。而《故事正義》和《表象背後》的共同之處則在於作者在討論古代法制論題的時候更多地依託了文學影視作品,這些作品涵蓋古今、涉獵中外。比如《表象背後》的第三部分“《西遊記》中探法史”,專門以《西遊記》中的故事來展開討論古代婚姻、孝行、復仇、盜搶犯罪等論題;《故事正義》中討論的作品對象則遍及《兒女英雄傳》《醒世姻緣傳》《清平樂》《大宋提刑官》《權力的遊戲》等,較爲適合作爲小說或影視劇愛好者的延伸閱讀。
值得一提的是,《表象背後》中“《拾穗者》與中西福利制度”一文爲讀者提供了觀察中國古代法制的又一視角——中西比較的視角。作者認爲,從法國現實主義畫家米勒的油畫作品《拾穗者》以及《聖經·路得記》中的律法故事來看,拾穗是上帝賜予窮人的一項權利,是爲了滿足人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中國古代《唐律疏議》中,在公私田園中摘食、棄毀、私自帶走瓜果蔬菜的行爲是觸犯刑律的,是被嚴格禁止的。作者還認爲,以上區別還與後世不同時期設計福利制度以及古代中國救濟制度密切相關,也影響了個人、社會、政府三者在提供生活保障或者救濟方面發揮各自功能時的不同設計走向。

米勒的油畫《拾穗者》背後包含的律法信息——拾穗是當時法國窮人的一項最低生存權利。
如果從中西比較的視角觀察中國古代法制,可以發現其本身就是一個獨樹一幟的存在,這也就是法制史學者們所說的與大陸法系、英美法系、伊斯蘭法系、印度法系並稱的中華法系。它泛指亞洲古代一些國家制定實施、在覈心精神與主體內容上具有共同特徵的法律羣,主要是指以中國唐代法律爲核心,包括東亞、東南亞一些國家通過移植、借鑑唐代法律而建立的古代法律羣。其中作爲中國古代制定法的最高成就,《唐律疏議》全面體現了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風格和基本特徵,成爲中華法系的代表性法典。
只是,隨着中國近代史的展開,隨着古代中國融入世界歷史的進程加速,自清末法制變革以來,中國古代法制中的大量制度和規則慢慢退出歷史舞臺,以大陸法系爲主體的西方法律典章、理論、術語則逐步被引進、移植進入中國,形成了近代法律體系的雛形。時至今日,社會大衆對合同、公司、法人等西方舶來術語早已耳熟能詳,對中國古代法制巔峯時期曾有過的“笞、杖、徒、流、死”的五刑體系卻可能渾然不知,甚至在一些學者看來,從今天現行的法律制度看中國古代法制,難免會生出一些“異域他鄉”的陌生感觸。
但必須看到的是,中國古代法制所彰顯的精神和傳統理念仍然在深刻地影響着目前現行的法律制度及其實踐,比如裁判者在辦理案件時要考量情、理、法的統一,比如調解息訟有利於社會和諧,比如善法與良吏相結合可實現法律的功能等,這些精神和理念古今同一。因此,從中西比較的視角觀察中國古代法制,一方面古代法制的傳統力量不容忽視,某項制度或者理念的產生和演變歷程就如同法律地圖上的座標,能夠爲後繼者指點方向,而不懂得傳統的人,猶如沒有地圖的旅行者,難以遠行;另一方面,自大航海時代東西方交匯進入新時期以來,那些被證明有利於國家進步、社會發展的知識、技術、制度、理念,那些能夠爲傳統中國向近現代中國轉型、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注入動力的法制力量,也同樣值得重視。唯不擇細流,江海方能成其大、成其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