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發現自己,在毀滅的火焰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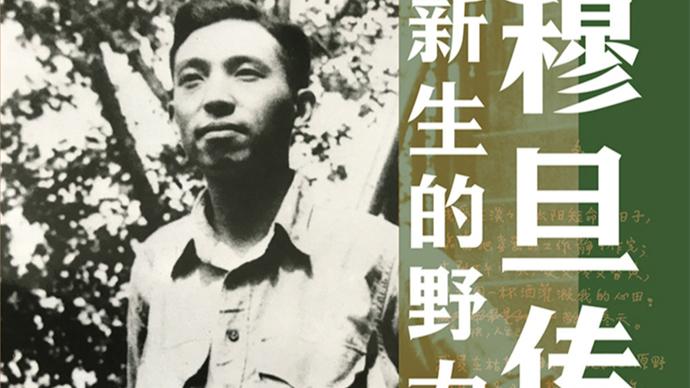

“一個沒有年歲的人站入青春的影子,重新發現自己,在毀滅的火焰之中。”“勝利和榮耀永遠屬於不見的主人”,這個主人是“虛無的時間”。這首詩寫於1947年,時年穆旦30歲,剛過而立之年的他已經九死一生,行走千里,經歷豐富,詩歌兼具理性與沉思的品質。雖然他的詩歌價值直到他去世後多年才重新被發現、被認定,但他的思想和榮耀一直都在。
穆旦出生於天津,祖籍是浙江海寧查家,是有名的望族,這也是出生在桐鄉的鄒漢明產生對穆旦探究興趣的原因。雖然據他考證,穆旦並沒有真正在海寧生活過,但是海寧一直以徐志摩和穆旦兩位現代詩人雙峯並峙爲傲。同爲浙江海寧人,徐志摩的傳記有幾十種,但穆旦的傳記可以說寥寥可數。比較重要的有陳伯良的《穆旦傳》(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出版)、南開大學教授王宏印的《詩人翻譯家穆旦(查良錚)評傳》(商務印書館2018年出版)、易彬的《穆旦年譜》《穆旦評傳》等。鄒漢明的《穆旦傳:新生的野力》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又多方走訪唐湜、鄭敏、來新夏、楊苡等穆旦的故交舊友,試圖呈現出多元立體的穆旦形象,釐清穆旦現代主義詩歌創作的內在思想理路,嘗試對穆旦的個體生命經驗與詩歌創作內在動力進行細緻分析。
該書通過多重視角的印證,建構起多重記憶場景。穆旦留下的回憶錄文字並不算多,特別是西南聯大師生西遷、野人山大撤退等慘烈回憶,穆旦本人並沒有太多細節追憶。鄒漢明通過同時代人的回憶錄、書信等資料,儘可能還原穆旦的學習與生活現場。通過趙瑞蕻的《南嶽山中,蒙自湖畔》、聞一多給兒子們的書信(《聞一多全集》)、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穆旦自己的回憶錄《抗戰以來的西南聯大》、王佐良的《一箇中國詩人》、周明道的《令人難忘的敘永生活》等,拼貼起西南聯大師生離開長沙前往南嶽再到昆明的學習和生活情況。這些史料展示了錢穆、湯用彤、吳宓、馮友蘭、金嶽霖、朱自清等文學大家刻苦研讀的場景,也說明了穆旦的詩人成長之路與他所接受的文學教育息息相關。抗戰勝利後,穆旦輾轉滬寧多地,作者也採證了黃裳、楊苡等與穆旦有過交往的朋友的書信、口述等材料,披沙淘金,鉤沉拾遺,拼貼起穆旦的生平軌跡。
《穆旦傳:新生的野力》在文學地理學的視角下縱向展示了穆旦的成長經歷,體現出戰時流動性的特殊空間體驗。抗戰爆發後,大批高校師生的撤退和轉移形成了全新的文學地圖和精神樣態,“行走”是穆旦詩歌生長的土壤,也是一種特殊的歷史際遇,諸多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大師、學者共同西遷南進,讓“讀萬卷書”與“行萬里路”同時實現,也使得穆旦的詩歌創作從一開始就紮根大地,具有宏大氣象。“七七事變”之後,北平陷落,在長沙設立臨時大學,清華學生結伴輾轉去往長沙。1938年日軍侵略湖南,南嶽分校結束,他們又徒步去往昆明。穆旦的《出發——三千里步行之一》記錄了這些行走的歷程。正是在祖國西南大地上用腳步丈量的這份深情,使穆旦的詩歌中擁有了厚重的家國情懷。正如《穆旦傳:新生的野力》書中寫到:“湘黔滇旅行團歷時68天,除車船代步、休息或受阻外,實際步行40天,除去乘船乘車,實際步行1300公里。平均日行32公里。這是戰時中國教育史上極爲動人的一幕。虛齡21歲的穆旦躬逢其時。對於一名詩人來說,要改變一個人的語言必須改變一個人的生活。正因爲由此不平凡的1300公里步行經驗,穆旦從此體會到了‘我們走在熱愛的祖先走過的道路上’。”也正因此,1941年12月,穆旦創作的《讚美》纔會如此氣勢磅礴、感人至深。《讚美》中的山巒村莊、河流森林、狂野的風、耕作的農夫……匯聚成無言而壯闊的場景,只有對這塊寬廣的土地有切膚的感受,才能寫出這種深沉的愛。
西南聯大詩人羣形成了戰亂中的精神高地,這“年青的昆明的一羣”是中國文學場域中一個特殊現象。在祖國遍地硝煙、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中國幾所著名大學的師生高擎精神火把,師長輩的聞一多、朱自清、馮至、卞之琳、李廣田等和學生輩的詩人們共同學習;同時,還有燕卜蓀、奧登等外國老師帶着西方現代詩潮觀念授課創作,給穆旦這批西南聯大學子帶來了思想和藝術上的沉潛與滋養。和穆旦同期的還有趙瑞蕻、董庶、楊苡等好友,他們成立詩社,談詩論藝,共同進步。在西南聯大的蒙自分校文法學院,朱自清、陳寅恪都在日記與詩作中書寫過蒙自的南湖,而穆旦也常和趙瑞蕻等同學在南湖漫步,修習功課,並積極參加南湖詩社的活動。穆旦大量閱讀英文原典,如雪萊、惠特曼、歐文、艾略特等,這些都深刻影響和改變了穆旦對詩歌的理解。作者通過對穆旦所在的文學場域的梳理,展現出穆旦詩歌寫作背後的空間、歷史和現實境遇,也說明了“中國新詩派”詩人羣出現的歷史必然性。
該書具有“詩史互證”的氣質,特別是在穆旦的戰亂生活與軍旅生涯中。1945年全民抗戰中,穆旦寫下了從內容到形式上都很成熟的《旗》。抗戰結束後,穆旦寫出了直面戰爭的詩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詩歌以復調結構,“森林”和“人”對唱,最後組成安魂的《葬歌》,以“峯頂靜穆的聲音”爲犧牲的英靈招魂。詩歌和史料的互證,呈現出穆旦詩歌語言的現代性、思維方式的現代化。
《穆旦傳:新生的野力》充分展現了哺育出穆旦式現代詩人的特殊時代。在移動的戰時空間,在民族存亡關頭,在國內外一流的詩人學者匯聚一堂的逃亡路上,在每時每刻都面對生死危機的極端情境下,穆旦創造出了一種全新的語言形式,用直見性命的現代白話照進現實。而遇到詩壇的不理解和攻擊的時候,同爲學院派的詩人們表達了對穆旦的深刻理解。對於穆旦的名篇《詩八首》,同期的詩人鄭敏認爲:“穆旦在40年代寫出這類感情濃烈、結構複雜的詩,說明中國新詩發展到40年代已經面臨豐收和成熟。”1947年,西南聯大外文系畢業的袁可嘉在天津《大公報》副刊《星期文藝》上發表評論,認爲穆旦代表了新傳統的追求。唐湜則認爲:“穆旦深沉的思想力,踐行了馬修·阿諾德的‘詩人必須進別人不敢進的窄門’,在絕望裏求希望。”這是阿甘本意義上的“同時代人”,他們既屬於這個時代,又在靈魂深處的撕扯中凝視這個時代。他們最終形成了“中國新詩”派(九葉詩派),成爲中國新詩現代化的一次羣體性的重要實踐。
一位詩人可能永遠都在尋找自己語言的故鄉。戰爭和行走經驗、西方現代派的中國傳播、複雜的現實與人性體驗,共同構成了上世紀40年代的歷史經驗,造就了現代新詩語言的革新和理性的抒情。穆旦1948年前主要是詩人,1953年歸國後將主要精力放在了翻譯上,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語言。《穆旦傳:新生的野力》是對穆旦的致敬,也是對我們這個多災多難而又堅韌不拔的民族的致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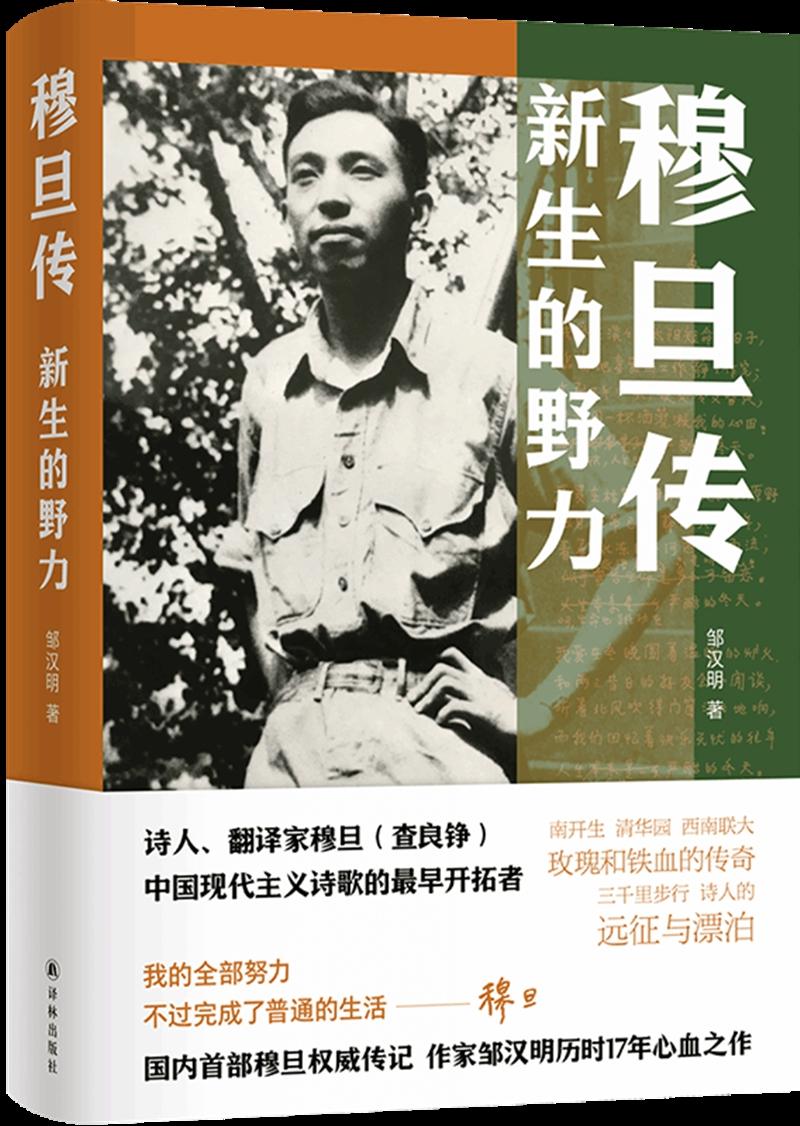
《穆旦傳:新生的野力》,鄒漢明 著,譯林出版社2025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