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父親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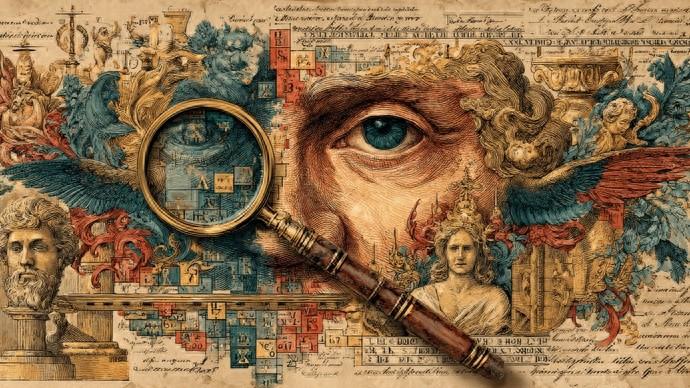

1943年6月的一天,好萊塢名人卓別林被告上法庭,原告是他曾經的弟子、23歲的女演員瓊·貝瑞,卓別林被指控是她剛出生的女兒卡羅爾·安的父親。
這場吸引人眼球的官司曠日持久,經歷了很多波折。血型分析發現,瓊是A型血,卡羅爾是B型血,根據血型遺傳法則,嬰兒的父親必然是B型血或AB型血,而卓別林是O型血,因此不可能是這個女嬰的生父。但是瓊的律師義憤填膺地指出,血型分析不足爲憑,因爲它只能排除一個不可能的父親,卻無法確定真正的父親是誰。1945年1月,經過三個小時的討論,由11位女士和一位男士組成的陪審團做出判決:卓別林是這個女嬰的父親,因此必須爲她提供撫養費,直到她21歲。
這場訴訟與其說關乎生物學,不如說關乎道德和正義。一邊是富有的社會名人,另一邊是不幸的年輕母親,情感的天平自然會傾向於後者。卓別林的父親身份並非源於他與女嬰之間的血緣關係,而是源於他與其母親之間曾經的親密關係。畢竟,從社會和法律的角度來看,這類親子訴訟的意義在於維護孩子的利益,賦予其合法身份和隨之而來的經濟保障。血緣關係固然要考慮,但是當血緣關係無法確定時,對於生物學意義上血緣關係的考慮就要讓位於社會因素的考量,即一方面要避免讓孩子成爲社會的負擔,另一方面要打擊不正當的男女關係。
現代親子鑑定技術出現之前,在這類親子關係訴訟中,要想確定父親的身份,只能通過觀察社會事實,即如果男被告與孩子的生母在之前的合理時間內發生過親密關係,就需要爲自己的行爲買單,承擔撫養孩子的責任。
這樣的邏輯並非這個陪審團所特有的,而是存在於許多社會的法律傳統中,並且有着十分悠久的歷史。就像哥倫比亞大學的米拉尼奇教授在《父親身份:探尋血緣之謎》中所指出的那樣,婚生推定原則不僅存在於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的法律傳統中,也存在於英美、歐洲大陸、拉丁美洲和中東的法律體系中,是“最接近文化普遍性的法律”。
1945年,一個名叫雷莫·奇波利的意大利男子起訴妻子通姦,並否認自己是她生下的嬰兒的父親,因爲一眼就可以看出,這個嬰兒是一個黑白混血兒。對於到底發生了什麼,當時很多人都心知肚明——二戰快要結束時,許多非洲裔美國士兵曾經駐紮在那一地區。這個嬰兒被稱爲“比薩的小摩爾人”,這件事也轟動一時。最後,民事法庭做出了一個令人震驚的判決,判定奇波利在法律上就是孩子的父親,因此要承擔與這一法律身份相應的一切義務。
在奇波利案中,大自然本身已經通過孩子的膚色揭示了父親身份的真相,但是法律選擇了無視這一真相。這表明人們一方面想要從生物學的角度來定義父親,並通過科學來確定生物學父親的身份;另一方面又對真相的強大後果心存忌憚。尤其是在奴隸制和殖民主義的背景之下,生物學意義上的父親身份不是被揭示的對象,而是被法律和政治所遮蔽的對象。
在奇波利案中有三個主角,分別是奇波利夫婦和混血嬰兒,第四個人物是缺席的,他就是作爲混血嬰兒生父的美國黑人大兵。在對這個案子的大量討論中,沒有一處揭示他的身份,甚至對他隻字未提。這種缺席並非偶然,因爲他的身份不僅是未知的,而且從一開始就被主動抹去了,而做出這一選擇的,不僅有意大利的法律,還有美國軍方的法律——阻礙美國士兵與當地婦女之間的婚姻。
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中,可以觀察到的生理學事實(懷孕和分娩)決定了母親的身份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父親的身份卻有着與生俱來的不確定性。父親身份之謎影響和塑造了人類的深層意識結構,成爲人類社會和心理的原始基礎。這一點在古今中外的神話故事和文學作品中都可以找到大量例證。從荷馬史詩到聖經故事,從《俄狄浦斯王》到《哈姆雷特》,從歌德、哈代到狄更斯、巴爾扎克和馬克·吐溫,父親身份之謎成爲一個永恆話題,它可以解釋人類社會的進化、現代經濟關係的興起、性別角色的變化以及人類心靈最深處的祕密。
在世界範圍內,父親身份的確定都十分重要,它決定着一個人是否可以繼承財產,是否可以擁有一個姓名,是否可以成爲一個家庭、社會和國家的成員並獲得相應支持。而在納粹統治時期的德國,父親身份決定了一個人的種族身份是雅利安人還是猶太人,進而決定了一個人的生死。
在19世紀之前,父親身份主要是根據父親對孩子的社會投入來確定的,尤其是婚姻狀況以及對孩子的撫養和支持,而這些主要依據的是社會網絡、口頭傳統以及父親對孩子本身的接受或拒絕。在19世紀,優生學提供了新的親子關係分析方法,包括身體測量、外觀相似性。20世紀初,隨着ABO血型系統的發現,血型檢測被用於親子鑑定。然而,就像在卓別林案中那樣,這種方法只能用於排除,而不能用於確認。分子生物學的發展開啓了鑑定親子關係的新時代,從1960年代的人類白細胞抗原(HLA)系統、1980年代的DNA指紋技術和聚合酶鏈式反應(PCR)技術,到1990年代的STR分析,再到21世紀的新一代測序技術(NGS),親子鑑定變得越來越精確,越來越快速。
現代親子鑑定技術似乎一勞永逸地揭開了籠罩在生物學意義上的父親身上的神祕面紗,讓人們可以確定無疑地瞭解自己的遺傳背景,突然之間,父親的身份變得不再神祕,確立親子關係、揭露出軌事件、找到失散的子女、解開嬰兒混淆之謎、發現一個人真正的種族和民族背景,這些都成爲可能。然而,就像作者指出的那樣,生物學真相的確立並沒有終結對父親身份的探索,科學上的確定性反而更加凸顯了父親身份的社會、文化和政治性。隨着大規模移民和城市化的發展、婚姻和家庭形式的多元化以及輔助生殖、胚子捐贈和代孕等技術手段的進步,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社會意義上的父親身份問題依然懸而未決,甚至會變得更加複雜。只有通過探索權力、性別和社會等級、觀念和慾望的歷史,我們才能理解、確定父親身份究竟是什麼。
可見,父親身份與家庭、性別、種族和國籍等因素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因此從來就不僅僅是一個生物學概念,還是一個政治、經濟、道德、法律和情感上的概念;不僅僅是一個涉及具體男人、女人、孩子和家庭的個人問題,還是一個涉及公共利益的社會問題。作者從全球史的視角,綜合運用了家庭史、社會史、文化史、科學史和政治史的寫作手法,將橫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檔案和記錄(包括科學檔案、法律文件和大衆媒體)巧妙交織到一起,爲我們呈現了父親身份的豐富內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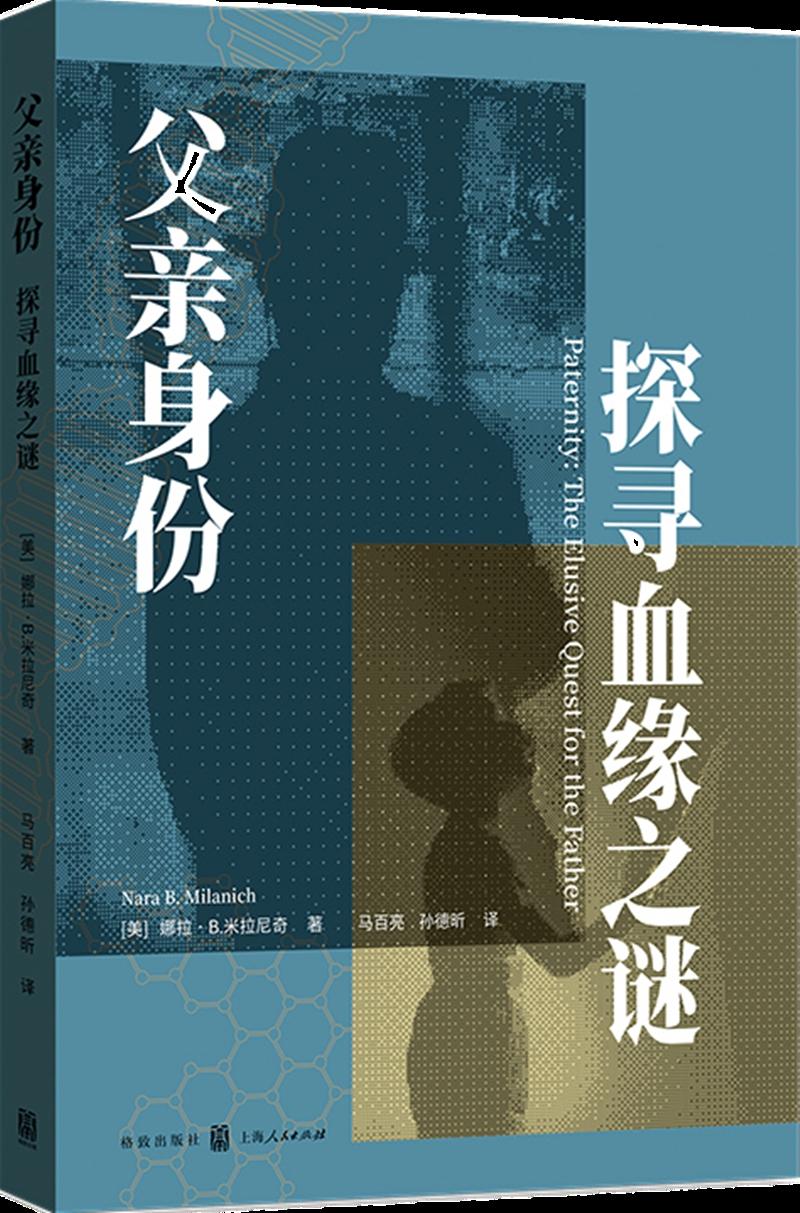
《父親身份:探尋血緣之謎》,[美]娜拉·B.米拉尼奇 著,馬百亮 孫德昕 譯,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