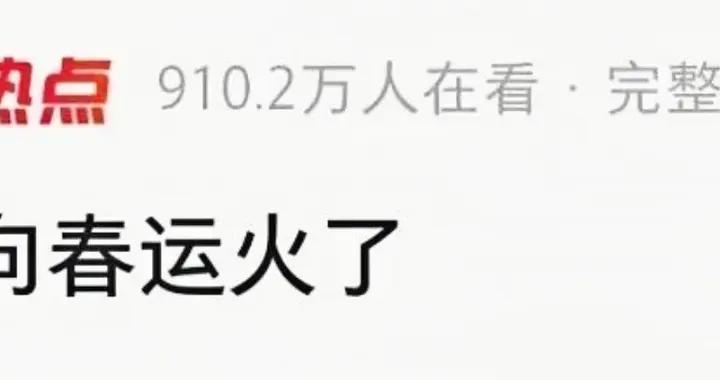影視劇不敢拍?《聊齋》後半段纔是蒲松齡的刀鋒所在!
列位看官,今兒咱不說那才子佳人的風月,也不表那沙場征戰的豪邁,單聊一樁怪事——爲何那熒幕上的《聊齋》故事,十有八九,都只唱了半出好戲?這戲臺子還沒涼,角兒就匆匆下了場,留我等看客捧着顆心,懸在半空,不上不下。殊不知,那被省去的後半段,纔是蒲松齡老先生嘔心瀝血,點醒世人的金丹妙藥!

就拿那婦孺皆知的《畫皮》來說事。影視裏頭是怎麼演的?無非是太原王生,路上撿了個天仙似的娘子,誰知是個青面獠鬼,描畫人皮,專害性命。最後必有那法力高強的道士或是高僧出面,拂塵一揮,寶劍一斬,妖邪伏誅,王生或許還能被救活,與那原配妻子相擁而泣,幕布一拉,皆大歡喜。這戲,熱鬧是真熱鬧,嚇人也真嚇人,可看完咂摸咂摸嘴,除了點人鬼戀的獵奇和降妖除魔的爽利,還剩下啥?
您且稍安勿躁,聽我細說。這影視劇拍的,不過是《畫皮》這出戏的上半闕,是那“奇譚”的部分,吊足了您的胃口。而蒲老先生原本的故事,在那惡鬼被誅之後,尚有洋洋灑灑三分之一的情節,那纔是“誌異”的真髓,是衝着咱們心窩子來的警世恆言!

卻說那日,道士收了那厲鬼,庭院血污遍地,王生已開膛破肚,死狀悽慘。其妻陳氏,悲痛欲絕,只得哭求道士搭救。道士嘆曰:“我法術尚淺,不能起死回生。指你一人,或能救你丈夫性命。”
陳氏忙問是何人。道士言:“市集之上,有一瘋癲乞人,常睡於糞土之中。你且去求他,他若百般羞辱於你,你萬萬不可忤逆生氣。” 列位,您聽聽,這高人指路,指的不是仙山老祖,卻是個滾在糞堆裏的瘋乞丐!這蒲老爺子,筆鋒一轉,便把故事從神怪鬥法,引向了人心試煉吶!
那陳氏救夫心切,真個尋到了那瘋丐。只見其人邋遢不堪,鼻涕三尺,正衝着路人癡傻嬉笑。陳氏跪地哭求,那瘋丐卻睜着渾濁雙眼,笑道:“美人兒,人人都可做你丈夫,救他作甚?” 陳氏羞憤,卻記着道士之言,忍辱再求。瘋丐愈發過分,竟用柺杖擊打她,又吐了一口濃痰在手上,遞到陳氏嘴邊,喝道:“喫了它!”

哎喲,您說說,這是何等的折辱!莫說一婦人,便是七尺男兒,也未必能忍。那陳氏當時面色如土,胃裏翻江倒海。可一想到丈夫開膛破肚的慘狀,她把心一橫,眼一閉,竟真個將那污穢之物強嚥了下去!只覺得那痰塊入喉,硬如棉絮,哽在胸間,上下不得,痛苦萬分。
那瘋丐見狀,拍手大笑:“美人兒真愛煞我也!” 說完,竟起身揚長而去,再不回頭。陳氏又羞又愧,回到家中,對着丈夫屍身,更是悲從中來。一邊哭,一邊想着方纔所受屈辱,越想越恨,直欲嘔出那心頭塊壘。正掙扎間,忽覺胸中那股硬物直衝而上,“哇”的一聲,竟吐出一物來,不偏不倚,正落入王生被剖開的胸腔之中!

您猜那是何物?非是那口濃痰,竟是一顆勃勃跳動的人心!那心在王生腔子裏滴溜溜轉了幾圈,旋即生出熱氣,漸漸與周遭血脈相連。不多時,那王生竟悠悠轉醒,傷口也奇蹟般癒合,只留下一道紅痕,如紅線纏繞。
故事到此,纔算真正了結。看官們,您如今再品品,這後半段,纔是蒲翁刀筆的真正力道所在!那前半段的畫皮女鬼,不過是外邪,是外來的誘惑與災禍,世人皆知該懼該防。可這後半段的“瘋丐賜心”,纔是直指人心的拷問!
那王生爲何招此大禍?乃因他色迷心竅,不辨人妖,引狼入室。他是“心病”了,失了“人心”!所以,救他的不是道士的神通,不是靈丹妙藥,而是一顆嶄新的“人心”!這人心從何而來?來自其妻陳氏的“忍辱”與“捨己”!

蒲松齡老先生在文末擲地有聲地嘆道:“愚哉世人!明明妖也而以爲美。迷哉愚人!明明忠也而以爲妄。” 那畫皮之鬼可怕嗎?可怕。但更可怕的,是人心中的那股淫邪之念,那股不識真心的愚昧!而最後救命的,並非外力,正是人間的至情至性,是妻子忍下天下至辱而換回的一顆赤誠之心!
影視劇爲何不拍?因爲這後半段不刺激,不香豔,甚至有些“噁心”,它需要靜下心來品,需要刺痛自己去悟。它把一個簡單的降妖故事,昇華成了對人性、對婚姻、對忠貞的一場宏大隱喻。它告訴你,真正的妖魔不在窗外,而在你我的心竅之中;真正的救贖,也非天降神兵,而是身邊那位你或許曾輕視、曾厭棄的糟糠之妻,她所能付出的,你無法想象的犧牲。
所以啊,列位,下次若再看那半部《聊齋》,您大可微微一笑,心道:“我已知那被剪去的真諦了。” 這,便是讀原著的妙處,便是與三百年前那位淄川老秀才,隔空對話的滋味。

一段《畫皮》真義,獻與諸位品評。正是:
表面文章繪鬼狐,皮相易畫骨難摹。
丹心須從污穢得,真諦總在幕後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