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周,所有《明日方舟》玩家都在試圖拯救一羣必死的NPC

怪物馬戲團 | 文
只要你打遊戲夠多,就會遇見“刁民”。很多遊戲裏,民衆都會被處理成一羣讓人高血壓的NPC,他們需要保護,死亡會使遊戲結束,行爲邏輯也匪夷所思。
譬如《冰汽時代》中,在極端暴雪裏決鬥的居民;或《都市:天際線》裏,無視你精心設計的路,執意堵車的市民。從某種角度上說,這種處理挺寫實,因爲人羣向來難以和諧共存,容易喪失理性。

過去,《明日方舟》也盛產“刁民”。有的NPC會不斷亂跑,死時扣血,也會協助敵人隱藏身份;他們甚至敢在BOSS發大招時,特意從掩體出來看熱鬧……
所以《明日方舟》的玩家對各種刁民,向來是聞之色變——直到最近,主題曲【反常光譜】的更新。

如果你關注相關話題,可能已經見過【反常光譜】引發的熱議了。從各方面來看,這都挺“反常”的。比如,繼實裝六星老頭子將軍後,《明日方舟》再次成了敢於實裝老奶奶戰士的二遊先鋒,鷹角在線下活動中,甚至爲她找了真正的高齡coser——而且卡池流水,排到了今年普池的第二,雖然流水不是真正值得關注的事。

你看過這次限時紀念活動的PV嗎?它甚至根本不像往常二遊的內容:你看到的是陰鬱肅殺的雪原,卡車用鏽跡斑斑的鋼鐵,載着一羣身影,越過監獄柵欄圍起的吊車,駛向凍土上的巨型礦坑。

失溫的東歐後朋配樂,映襯着一把砸向冷硬岩石的鋤頭,看不清是血或淚的液體落向大地……當配樂被合成器推向高潮時,搭配的也不是幹員展示畫面,而是一羣模糊瘦弱的身影,在黑暗的礦洞中鑿出了憤怒的、晦暗的火。

就連大家討論的高光片段也有點反常,很多都和具體幹員無關。人們轉發一張長CG,上面是彌天大夜,一羣沒有面孔的人,在冰原上點燃火把,走向遠方不祥的暗紅軍隊。

另一個被許多玩家討論的片段,是一名傷痕累累的礦工父親,發現離家的兒子成了殘害礦工的守衛,隨後的故事沒有原諒或眼淚,只有發了瘋般呢喃說這不是自己兒子的父親,拿着刀,顫抖地問對方爲什麼披着兒子的面具和皮。問話只換來了一片沉默,然後是一道血紅。

但最反常的,還是方舟一改過去的“刁民”機制。一些skip黨玩家說,他們在進入關卡後立刻感覺不對勁,趕緊切出去重看劇情來了解機制。因爲這次NPC們不再逃跑了,相反,他們一邊高喊活着,一邊毅然向敵方衝去,戰鬥至死,源源不斷。

每一關,你都會和這些礦工們並肩作戰,你需要他們幫忙開路驅散迷霧,他們會幫你攔住無法阻擋的敵人,幫你清理污染。在強敵面前,他們會拼死替你擋住進攻,你纔能有間隙部署幹員。
要獲得勝利,必須要犧牲,大量的犧牲。關卡里幾乎不可能保全所有人,這些礦工可以被治療,但哪怕你放上多位醫療幹員,他們還是會大片地死去,有時,你甚至需要看着他們去送死。可縱使如此,他們也會義無反顧地前進,沒有人的死亡會讓遊戲扣分,彷彿他們爲之而戰的並非生命。

最後幾關,礦工們不斷從後方湧出,前赴後繼地衝鋒,和你並肩面對鋪天蓋地的強敵。與其說最後是BOSS關,不如說,它是個特殊關卡。
【反常光譜】,應該是我心中今年最好的二遊內容。

這些礦工,是一無所有的奴隸。他們被剝削了身份,被送入暗無天日的源石礦井,身上裝着爆炸芯片,被迫日夜開採礦脈,只爲滋養烏薩斯強大的軍隊,以及尋歡作樂的貴族。

從很多細節上,你都可以看出這個設定的影子。礦工不會在任何強敵前退縮,但其實根據圖鑑,他們的生命值極低,重量只有0;相比之下,過去的“刁民”重量基本都是1。可能是因爲這些礦工常年飢餓,虛弱得像一個個沒有重量的鬼魂。
很多人都調侃說,國內二遊一旦寫蘇聯/毛子的相關題材,就會開始在文案和音樂上超常發揮,做出你無法在歐美日韓的二遊裏見到的東西。那我覺得《明日方舟》的烏薩斯故事線,就是這個現象的典型代表。

在我心中,《明日方舟》最精髓的部分之一,的確就在其烏薩斯故事間。因爲這些故事不是隨意寫出來的,你可以看出鷹角真的一直在深入探尋斯拉夫文化的內核,所以烏薩斯故事,總是能帶上一絲斯拉夫文學的韻味。
早年互聯網對蘇聯和俄羅斯人的刻板印象,基本來自歐美文化裏嘲諷的“俄式鬼畜”,總和戰鬥民族單手做俯臥撐、用土嗨電音跳蘇卡布列舞掛鉤,很少有人看到俄羅斯真正盛行的,迷茫冷冽的doomer文化。

老玩家或許記得,當時網絡上關於烏薩斯干員們,也就是“熊團”的二創,基本都是這種醉酒毛子的搞笑感。
但其實早在那時,方舟的烏薩斯故事就不是這種刻板基調。他們爲烏薩斯選擇的音樂,從一開始就源自斯拉夫的土壤,沒有任何土嗨電音,而是從手風琴上的斯拉夫民謠,到憂傷的俄語搖籃曲,直到這次的東歐冷潮/後朋。
它們讓你想起的不是油管熱門鬼畜,而是柳拜樂隊的《這裏的黎明靜悄悄》。
最初,我其實不怎麼喜歡方舟的故事,而徹底改變我看法的,正是「烏薩斯的孩子們」。我相信這也是很多人第一次意識到,《明日方舟》這個遊戲想表達的東西並不普通。

那個活動說的是遊戲裏“熊團”的故事,她們是一羣流亡的烏薩斯少女,最初很多玩家以爲她們的形象是動漫化的,像日常番裏的角色:肩扛街頭音箱的“凜冬將軍”、吐槽役文學少女真理、熱愛烹飪的丸子頭古米……
可熊團真正的故事,卻現實而寓言性。她們的學校在整合運動引發的動亂中被封鎖,食物短缺,無法逃離,於是這些貴族或貧民孩子們,就在這個被封閉的地獄裏逐漸墮落,互相爭鬥、廝殺。

健康人和礦石病人爭鬥、貴族和貧民爭鬥、飢餓的人和有食物的人爭鬥……當烏薩斯的孩子被羅德島找到後,都留下了一些怪誕的習慣,源自身後的死亡和飢餓。
表面無所畏懼的凜冬將軍不斷做夢,來自過去的,黑暗殘忍的夢。她在夢裏看見過去的自己爲了爭搶食物,不慎打翻蠟燭引發大火,燒燬糧倉導致了災難。

看似優雅,出身高貴的早露,則想起自己曾在封鎖的學校裏,如貴族家長般腐化,引導一波波對其他孩子的掠奪。她過去無情的自己、負罪的自己一次次找到她,逼迫她在夜裏嘗試自盡。

……
當時有個著名的討論:玩家一直爭論文案是不是暗示熊團的古米,在飢餓和動亂中喫過人,或殺了生,所以她才無法剋制在第三下攻擊時用勁。

我覺得,真相其實不是重點。因爲在故事刻畫的那個地獄裏,一定有另一個古米會喫人,有另一個古米會殺生,而正是因爲這個地獄的存在,我們的古米纔會選擇戰鬥。一個象徵性的巧合是,作爲遊戲開服角色,許多玩家至今也依舊會在集成戰略讓她參戰。

烏薩斯孩子們的童年是被錘鍊消失的,她們的故事也無法俗套地從黑暗走向光明,因爲它有着斯拉夫文學那被歷史浸染的一面:光明不會這麼容易降臨,斯拉夫人的文學,也不是關於光明驅散了黑暗,而是關於人從被黑暗窒息,到起身面對它。
一旦方舟回到烏薩斯,就會讓你想起斯拉夫人的故事,貫穿多個時代。實際上,《明日方舟》敘事的起點之一就在烏薩斯。強大的烏薩斯是一臺不斷侵略的戰爭機器,爲了處理戰爭留下的狼藉,他們對內高壓,激化礦石病患者和普通人的矛盾,才導致第一個“反派”整合運動的產生。

代表烏薩斯之魂的黑蛇,利用虛僞的公平誤導人民,讓烏薩斯人變得強大、無情,一切如寓言般進行。
這裏有斯拉夫文化裏的聖愚,有蘇聯式的赫魯曉夫樓,還有蘇聯辦事風格的敵人,會臨時頒佈禁令來逮捕主角。

你看到的礦工也是斯拉夫式的,他們的勞作支撐起烏薩斯的命脈,但他們會被遺忘在烏薩斯的塵土下。在劇情中,你能看到貴族們討論鞭打他們取樂,如何用額外的酬金,在鞭子上添加刀片和鹽水。
這是一羣沒有食物,沒有人權的奴隸;是沙俄的農奴,讓二月和十月燃燒的火種。

沙俄的農奴們都死了,但沙俄的農奴們都活在高爾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果戈裏的文字裏。在烏薩斯的故事裏,你總是能見到這些斯拉夫文豪留下的影子。
方舟的烏薩斯故事,經常讓我想起蘇聯文學的兩座高峯:《癌症樓》與《靜靜的頓河》。它們分別以不同立場獲得了諾貝爾獎,在現實也落向不同的結局。
《癌症樓》說的是蘇聯政府的高壓下,一羣來自不同階級,有不同思想和道德的人,被癌症聚到了一起。然後這羣罪惡、不識字、酗酒和憤世嫉俗的人,開始在癌症樓中,從托爾斯泰的字裏行間尋找人爲了什麼而活着。

《靜靜的頓河》,則記錄了哥薩克人的史詩。敢愛敢恨的哥薩克人,無所畏懼、驍勇善戰,卻迷失在飄搖不定的時代中。他們支持過白軍,也曾加入紅軍,有時是侵略者,有時又是受害人。他們踏過一戰、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最後終於走向俄羅斯大地上的滄桑鉅變。

《明日方舟》的礦石病,就像《癌症樓》中的腫瘤,它們說着相似的故事:苦難中,一羣身患絕症的人尋找該爲了什麼而活着。放眼望去,泰拉大陸上的戰爭和世仇,也像是另一種屬於文明的,更大的癌症。
在【反常光譜】中,人們因感染礦石病被送去礦區,隨後他們的孩子也將被礦石感染,如此惡性循環,永無止境,宛如所有人都被困在一棟癌症樓中。

而烏薩斯人的故事,也像是哥薩克人的故事。烏薩斯人有着哥薩克人的野蠻,他們四處征服、然後被理想分裂,留下熾熱的、破碎的回憶,就彷彿遊戲裏迷茫的整合運動。
“連年的征戰使他疲憊不堪,只想避開這個沸騰着仇恨、敵對和難以理解的世界。身後的一切是一本糊塗賬,互相矛盾,想找出一條正確的道路太難了,就好像走在沼澤中的小路上,腳底的土地在搖晃,路也在消失,而且是否應該走這條路——也毫無信心。”

這是肖洛霍夫寫下的文字,它也可以用來概括方舟的烏薩斯故事。
在《靜靜的頓河》中,所有人都是有罪的,可罪惡中,又有着某種令人難以斥責的悲愴之物,雪霰般覆蓋在被戰爭遺忘的瓦礫間。方舟裏的烏薩斯“反派”們亦是如此:浮士德、梅菲斯特、碎骨、米莎……

但神奇的是,幾乎所有斯拉夫人的著作,不論立場如何,不論怎樣躊躇,也都會堅定地藏着一份穿透隔閡的光芒,就像永不會被冬日掩蓋的太陽。這讓斯拉夫的文豪們總是懷抱一種古老的信念,根植於他們的血液中,讓他們夢想拯救自己,然後,拯救與解放人類。
《靜靜的頓河》之所以偉大,是因爲它讓哥薩克騎兵跨越了所有他們馳騁的戰爭,讓某種更高之物從這奔騰的馬蹄中浮現,超越所有的立場和時代。

而在壓抑的《癌症樓》裏,一個沉默渺小,不斷被壓迫的圖書管理員,在和死亡對決前說出了全部的心聲,他用痛苦、氣餒、怨恨和眼淚喊出了全書的高潮,然後他說:“去他媽的仇恨,我們終於要相愛了——社會主義就該這樣!”
「烏薩斯的孩子們」中,苦艾在暴亂的城市裏走過火焰和廢墟。放眼望去,只有死亡和罪惡,可她卻想起了父親和母親的約定:等到了烏薩斯的春天,郊外的雪開始融化,他們會一起在原野上跳舞歌唱,那片斯拉夫人的,自由激情的,廣袤的原野,有無盡的山脈和燦爛的冬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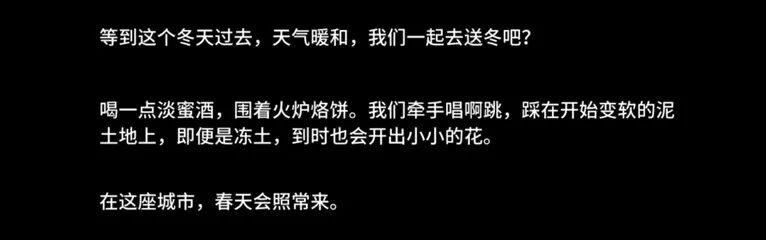
這個約定帶着烏薩斯的孩子們,來到了羅德島。
就像之前說的,方舟的烏薩斯故事,總讓我想起柳拜樂隊的歌:記住過去,記住戰爭和痛苦,但是也記住隨着哥薩克的舞蹈抬起你的雙腿,拉開你的手風琴。

所以在故事最後,你會相信這羣烏薩斯的孩子們,將學會揹負陰霾活下去,也許成爲英雄。永遠矛盾的斯拉夫人,確實向來是一個盛產英雄的民族,他們掀翻過一次暴政,然後抵擋了一次入侵。

爲了解放人類,你必須先相信人類。所以斯拉夫的文學,是由過去的血寫成的,但它寫的是明日——這是斯拉夫文學真正的內核,也是方舟烏薩斯故事線的真正內核。
這個內核在【反常光譜】的故事中赫赫燃燒:它說的是一羣無路可走的礦工起身反抗壓迫,可他們的反抗被利用了,就像曾經的整合運動一樣,被冠以崇高的目標,然後引向恨和毀滅。

但這些礦工身上的苦難,卻讓他們逐漸擺脫控制。他們曾飽受掠奪,所以就算在困境中,也不願打劫村莊;他們揹負過太多仇恨,所以在即將脫繮的審判中,沒有選擇讓仇恨蔓延。
在邪魔的操控下,這些礦工一擁而上,打倒了烏薩斯駭人的內衛。這是讓人熱血澎湃的傳說,因爲內衛腳下的黑霧,叫作“國度”,而如今將它壓制的是“人民”;因爲內衛的名號叫“皇帝的利刃”,它彷彿註定要被一無所有的礦工推翻。

然而這些源自勇氣的傳說也會被扭曲,帶着礦工們走向黑暗。直到開頭所說的,那個弒子的父親用心碎的經歷,留下了殘忍的寓言:證明了仇恨只會導致更多仇恨,哪怕以崇高爲名。

就如同斯拉夫文學的故事,礦工們在苦難中學會了憤怒,怒火在雪境中幫他們點燃了希望;然後在燃燒的暴動中,他們意識到,救贖必須超越肆虐的火焰。

這時那個貫穿斯拉夫文學史的主題纔會浮現:生命的選擇,從來不是選擇生或死,因爲生命是會本能去選擇活着的;生命的選擇,是爲了選擇爲何燃燒,才能不愧對死亡。
斯拉夫文學的光芒終於照了進來:疲勞的礦工們在夜裏起舞,拉起手風琴,唱起了那些屬於過去的烏薩斯歌謠——短暫而平淡,但有某種信念因此迴歸了。

在烏薩斯的故事中,鷹角總是在象徵性地運用斯拉夫歌謠:浮士德和梅菲斯特在死後失去了戰鬥的代號,重新用斯拉夫式的名字:薩沙和伊諾,睡進了一首俄語搖籃曲。

當整合運動瓦解前,它的良心也化作白色的兔子躺倒在玩家手中,留下一首屬於她的斯拉夫輓歌。

總是歌謠,因爲歌聲對抗的是沉默,沉默是屬於死亡的,而歌謠代表着生命。
所以當角色歌唱古老的烏薩斯民謠時,有人問她唱的是什麼,她回答說:是愛。

於是礦工們放棄了沉默,這沉默是與烏薩斯正規軍對抗的未來,然後在少年敲響的鐘聲中選擇了另一條路。

這條路是殘忍的,烏薩斯的軍隊開始轟炸礦坑,用屠殺掩蓋礦脈枯竭的消息。而礦工們在冰原上點燃了火把,向着他們走去,爲了戰鬥,爲了用自己吸引炮火,爲了那些更年輕的礦工們存活。

那些你在先前故事裏熟悉的角色們,在此刻失去了面孔,他們轉身向着烏薩斯不敗的軍隊走去,你只能通過畫上的背影模糊地看見他們。這支隊伍中有人逃跑,有人背叛,有人畏懼,但隊伍沒有後退,它將你引向文章開頭那場,無數礦工和玩家並肩作戰的特殊關卡。

爲什麼礦工NPC死後不會扣分?不是因爲廉價,而是因爲在戰爭中,你總是看不清有多少人犧牲,但他們不是爲了活着而戰的。
【反常光譜】的故事在這場戰爭中觸及高潮,可是沒有角色的榮光屬於戰鬥。幹員真言的高光片段,是她用聲音刺破烏薩斯的訊號屏障,把死者的呼救,和屠殺的真相傳向泰拉。

這個故事的高光屬於文字和聲音,屬於暴行前的高喊:我們正在被屠殺!不是我們背棄了烏薩斯,而是烏薩斯拋棄了我們!
然後這高喊告訴妄圖用強權扼殺生命的人:知識比王權恆久,真理比謊言強大。
戰爭最後,阿米婭在罪惡前拔出了憤怒的劍,她沒有劈向任何人,而是斬斷了戰場。身爲孤兒的阿米婭是這個遊戲的女主,她是所有血統論傳奇主角的反面,一個泰拉大陸的孩子,或者說,生命的孩子,現在也在故事裏留下了自己的聲音,這個聲音說:“即使我不報復也不懷恨,我也有永遠憤怒下去的權利。”

爲什麼?因爲世界不夠美好,因爲人心太過冷漠,因爲文明太過弱小,因爲災難太過強大。
因爲人們必須前進,因爲斯拉夫文豪們一次次用故事寫下的真理:因爲生命必須前進,人性必須前進。
故事結束後,遊戲會觸發一個特別關卡,裏面沒有戰鬥,只有一面烏薩斯的紅色旗幟,但上面被礦工們塗上了他們的標識。

旗幟之下,烏薩斯的熊團,透過灰燼下的天空守望黎明。她們帶着希望和痛苦,走到了這裏,在這次的故事中,幾乎見不到她們的身影,可還是能觸碰到多年前,我們在「烏薩斯的孩子們」中看到的靈魂。
因爲這些礦工們,其實也是勉強長大的烏薩斯的孩子們,試圖守護另一羣更年輕的烏薩斯的孩子。
在《靜靜的頓河》中,肖洛霍夫寫道:凡是戰爭烽火燒過的地方,凡是哥薩克馬蹄踏過的地方,到處都會留下腐爛的哥薩克屍體。這正是方舟整個烏薩斯故事線的畫像:彷彿永無止境的動亂中,烏薩斯的孩子們不斷逃亡,迷失方向,在切爾諾伯格的街頭間躲藏,被火焰和死亡賦予一種扭曲的成長,烏薩斯式的成長。
“哥薩克的精華都背井離鄉,死於戰火、蝨子、恐怖和無法排遣的憂傷。”帶着這句話,你也許更能理解【反常光譜】的PV中,那句出現在黑暗前的文字:
“偉大的烏薩斯,坐擁萬物,卻一無所有。”

在【反常光譜】中,一個角色感嘆說:烏薩斯是如此落後,所以它是如此悲哀。你如果瞭解斯拉夫人的歷史,會意識到這句話同時也是斯拉夫人的寫照,這個彪悍的種族直到千年前才真正找到自己的語言,哪怕在托爾斯泰的時代,很多上層詞彙,也只有法語,所以《戰爭與和平》裏最高雅的段落都是法語寫成的,俄語屬於痛苦和離別。
但斯拉夫的文豪們,卻用這個不成熟的語言寫下了兩雙屬於自己的手臂。第一雙手臂支撐着烏薩斯的敘事骨架,所有的愛與生命、恨和死亡,都會被這疲勞的雙手交給那片冰冷無情的土地。

《士兵之歌》(蘇聯),也是《電鋸人》中,讓瑪奇瑪落淚的電影
而另一雙手,就像是《癌症樓》中的那一幕:一個女孩向死前的少年俯身,她說着那些關於愛和天空、此刻和萬物的話語。索爾仁尼琴寫道:她雖然沒有伸出手,卻好像伸出了兩條臂膀,穿過大地上所有的斷壁殘垣,將萬物囊括。

這雙手也托起了烏薩斯故事線的真正靈魂,它讓那個領導礦工的人,慢慢放下極端的仇恨,問出了那個問題:你們見過烏薩斯的春天嗎?
“我見過,”他說,“冰雪會消融,土地會再次長出綠草,遷徙的羽獸會再次回到烏薩斯。”

《這裏的黎明靜悄悄》
在冰雪之下,就是靜靜的頓河。森林枯萎、戰場燃燒又化爲餘燼,一代代人,左右搖擺、躊躇不前,跨越了戰爭和幻滅,最終走向了某種更高的事物。而透過扭曲的空氣和被遺忘的塵埃,後世的人也從這個民族身上看到了某種啓迪性的,普世的深遠之物。
人類的歷史,一次次重複迴旋,斯拉夫人留下的文字便在其中流淌,敲着警鐘,映照着太陽和遙遠的歌謠。斯拉夫人的雪和血,長夜與火焰,全都凝聚在這首歌謠中,一切都在流動,宛如酒精,宛如頓河的浪濤,冰和搖曳的松衫。

頓河河畔,爲肖洛霍夫著作建造的蘇聯雕塑
這歌謠唱着血管裏的冰,唱着千年的迷茫、罪行和征戰,它也唱着革命的火。
這首歌謠會讓你的靈魂浸泡在酒中,眼睛透過革命的灰燼,望向燃燒的詩歌與歷史,火焰與冰雪,莫斯科的鐵軌與聖彼得堡的天幕。歌謠響起後,雪會從烏拉爾山脈滑落,讓你在地下室的死屋手記中望見太陽,來自一輪堅定永恆的冬日,那是斯拉夫文學不滅的光輝。
你總是能從《明日方舟》的烏薩斯故事中,聽到這首古老的歌謠,我想,這也是它之所以動人的原因。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