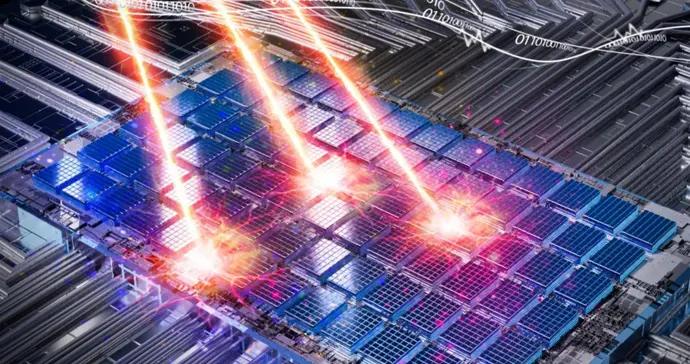互聯網大廠興建美術館意味着什麼?



過去幾年,企業美術館,尤其是地產系美術館遭遇寒冬,像OCAT上海館、上海喜瑪拉雅美術館、青島西海美術館等先後關閉。沒想到,企業美術館的另一個分支,互聯網大廠系的美術館卻在寒冬中紛紛崛起。
就在上個月,京東集團正式宣佈成立京東美術館(JD Museum),落戶深圳灣總部基地,建築面積超一萬平米,按照計劃,它將在2027年底開館。巧的是,騰訊的“騰創未來”藝術館目前也在深圳灣如火如荼地建設中,與京東美術館正好隔空對望。
通常來說,企業涉足美術館的建設與運營,其目的和動機是多維的和戰略性的。比如提升品牌形象、拓展市場、開展差異化競爭、激發企業創新活力、增強內部凝聚力和文化認同感、以及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和實現公共價值等等。
當下,中國互聯網科技企業興建美術館,除了上述這些傳統訴求之外,更可能成爲融合科技與藝術、線上與線下的新型文化平臺。在技術紅利觸碰天花板的今天,藝術正在成爲科技巨頭的破局之力。

京東美術館示意圖
經濟資本向文化資本的轉化
放眼全球,企業參與藝術建設早已形成成熟模式。
比如洛克菲勒家族的藝術基金會,不僅創立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還在全球範圍內支持藝術項目,建立了長達百年的文化影響力;奢侈品巨頭LVMH集團,通過其旗下的路易威登基金會,進行展覽、收藏、建築贊助和國際項目,系統性地推動現當代藝術發展;三星集團不僅在首爾創立Leeum 三星美術館,並多次贊助威尼斯雙年展韓國館;現代汽車集團自2015年起,成爲英國泰特現代美術館“現代汽車系列之泰特現代渦輪大廳委託項目”贊助商,該系列是全球當代藝術界最具影響力的年度展覽之一,吸引數百萬遊客;豐田公司的豐田美術館不僅收藏了大量日本傳統工藝品,還積極推動當代藝術發展,成爲企業長期推動文化藝術的典範。
反觀我們國內,經過前幾年的飛速擴展,如今,京東、騰訊等互聯網大廠的發展進入平穩期,科技的優勢已不再像過去那樣懸殊,企業需要藉助“軟實力”來構建更高維度的品牌認同。而藝術所具備的直覺、情感與敘事能力,恰好彌補了科技理工思維的侷限。
有人說,技術的盡頭是藝術。的確,藝術作爲一種“高級語言”,能夠幫助企業與消費者建立超越商業交易的情感連接。當下,藝術正在成爲品牌升維的重要載體,爲科技品牌注入人文厚度與情感溫度,塑造更具包容性與影響力的文化身份。
事實上,京東與騰訊這些互聯網企業,前期他們憑藉着技術優勢和商業模式積累了大量經濟資本,他們興建美術館,某種程度上可以將其視爲把經濟資本轉化爲文化資本的一種策略。通過資助藝術、收藏作品、打造文化地標,這些互聯網企業可以擺脫“純粹逐利”的刻板印象,有效提升企業的品牌格調,幫助企業在消費者心中建立“藝術+商業”的複合認知,增強公衆好感度,建構一種具有社會責任感與文化使命感的良好形象。這種轉化有利於這些企業在文化領域獲得話語權,重塑自身在社會等級中的地位。
互聯網大廠興建美術館,其實質是商業精英闖入文化場域的典型行動。
文化場域原本由藝術家、評論家、公立機構等主導,而互聯網資本的介入改變了場域內的權力平衡。企業憑藉經濟實力重新制定規則,比如推崇與他們自身產業關聯的藝術形式,爭奪藝術的話語權。這一過程反映了中國新興科技資本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他們在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後,便有了文化的訴求。同時也折射出全球化背景下“資本文明化”的普遍邏輯,通過文化資本的積累,完成階層躍升的最後鍍金。
值得注意的是,美術館不僅是文化空間,更是社會資本的樞紐。企業通過藝術展覽、贊助獎項、學術論壇等活動,聯結藝術家、策展人、收藏家、媒體等文化精英網絡,形成利益與聲望同盟。這種網絡進一步轉化爲象徵資本,企業被賦予“文化貢獻者”的光環,公衆對其商業實踐的批判可能會因其文化貢獻而被淡化與弱化。
數字時代新型文化資本形態:從“實體收藏”到“數字生態”
如果我們要識別數字時代新型文化資本的形態及其生產邏輯,那麼這些互聯網大廠的美術館實踐,恰恰是我們能看到的這種新型文化資本的“實體化接口”。
互聯網企業的核心優勢是數據與算法。它們興建美術館,並非僅僅展示傳統繪畫雕塑,而是大量推動科技藝術、數字藝術、AI生成藝術。更爲重要的是,它們將基於數據與算法,平臺與流量,開創全新的策劃、運營、推廣模式,實際上是將企業的技術資本,比如數據、算力、算法等轉化爲新型文化資本和審美資本,即數字化的審美與敘事能力。誰能定義未來藝術與展覽的形態,誰就掌握了數字時代的高階文化資本。
以往文化權威是美術館或博物館館長、評論家、策展人,而在數字時代,平臺擁有強大的“策展權”。平臺將決定什麼內容被看見、如何被分類、與誰關聯,而他們的線下實體美術館只是這種平臺策展能力的線下延伸與合法化。企業通過線下展覽,將其線上固有的“流量分配”與“內容策展”邏輯,賦予其神聖的文化藝術光環。
新型文化資本不僅重視擁有什麼藏品,更重視能提供何種沉浸式、交互式、可傳播的體驗。互聯網大廠的美術館往往極具設計感,強調“打卡”體驗和社交媒體傳播。因此,未來能否創造並主導引領潮流的文化消費場景,將成爲區分新舊文化精英的標誌。
推動傳統企業美術館進行範式更新
傳統企業美術館的核心是建立企業收藏並定期舉辦展覽。模式相對傳統,類似一個“企業內部的公立美術館”,強調學術性和藝術價值。並且其運營獨立於核心業務,與主營業務關聯度弱。觀衆是“參觀者”,用戶是“藝術愛好者”,其影響力主要集中在藝術圈和本地文化領域。
而京東、騰訊等科技巨頭興建美術館,它們帶來的不是簡單的“升級”,而是一種範式更新,將美術館深度融入其數字生態和科技基因。這些美術館不再是孤立的品牌項目,而是其龐大的科技、電商、社交、內容生態中的一個關鍵線下體驗入口和內容發生器。
比如京東美術館可能是其“線下體驗戰略”的重要一環,與家電、家居、圖書等品類體驗深度結合,打造高品質生活方式的目的地,反哺線上消費和會員體系。而騰訊的“騰創未來”藝術館,將是其“科技+文化”戰略的實體化身,是其連接用戶、藝術家、IP、以及遊戲、音樂、影視等數字內容的 “實體樞紐” ,旨在培育和孵化數字文化創意生態。
如果說,傳統企業美術館是以藝術史、策展人視野爲核心驅動,那麼,科技企業美術館是以科技、數據和用戶體驗成爲核心驅動力,展覽本身可能就是一件大型“數字藝術品”或“社交實驗場”。
衆所周知,展覽天生具有“社交貨幣”和“打卡”屬性,通過微信、視頻號、小紅書等社交工具獲得病毒式傳播,線上流量反哺線下。像京東美術館,可能深度融合其物流供應鏈、線下沉浸式零售體驗、線上直播導覽與電商直接轉化。參觀體驗可能通過App無縫鏈接,實現藝術品或衍生品“看到即買到”。
如果說,傳統企業美術館面向的是“藝術公衆”,那麼科技企業美術館面向的是其海量的線上用戶。一個微信用戶、一個京東PLUS會員,可以很自然地成爲美術館的訪客。他們的參觀行爲、偏好數據會被納入龐大的用戶畫像體系,形成更精準的服務閉環。觀衆不僅是觀賞者,更是數據提供者、內容共創者和生態參與者。
因此,如果說傳統企業美術館是“業務之外的文化飛地”,而京東、騰訊的新美術館則是“核心生態之中的文化芯片”。前者是用企業的資金服務藝術,本質是藝術邏輯;後者是用科技和生態的思維重塑藝術體驗與生產消費,本質是商業邏輯。

騰訊美術館示意圖
批判性反思:挑戰與潛在風險
互聯網大廠興建美術館,也存在着一些挑戰與潛在風險。
首先,科技企業的美術館可能更注重“流量數據”“用戶增長”“生態協同”,導致展覽策劃偏向大衆化、網紅化,削弱學術深度和批判性。
科技公司擅長的“標準化產品思維”可能導致展覽模式趨同,削弱美術館的獨特性和地域文化特色。而互聯網文化追求的“迭代速度”,可能導致展覽趨向快消式體驗,削弱藝術的沉思性與批判性。過度依賴技術可能導致展覽“過濾”掉不善數字工具的羣體,形成新型文化區隔。
與此同時,頂級藝術家和策展人資源可能向資本雄厚的科技系美術館集中,加劇資源分配不均。更有甚者,科技巨頭的場館可能在資金、媒體關注、公衆流量上對中小型美術館形成“虹吸效應”,擠壓其生存空間。
其次,藝術成爲企業生態的“引流工具”或“品牌包裝”,而非獨立的文化批判場域。企業主導的文化生產可能將藝術轉化爲品牌營銷工具,展覽的主題也會更傾向於貼合企業敘事,從而削弱藝術批判現實的可能性,是對藝術自主性的一種侵蝕。科技企業一般更依賴於數字特效,將可能出現大量“沉浸式展覽”跟風潮,從而擠壓傳統媒介、實驗性、思辨性藝術的展示空間。
再有,儘管這類美術館也面向公衆,但其最終服務於企業戰略。此類美術館不再是純公益屬性,而是能通過IP運營、數據價值、生態聯動等方式的一種商業模式。因此,科技巨頭通過建構數字時代新文化貴族的身份,實際上是將經濟霸權延伸至文化領域。觀衆在這類美術館中的行爲數據可能被科技公司收集,用於商業分析,引發對藝術體驗被“數據化監控”的倫理爭議。
綜上所述,國內美術館生態能否形成 “科技巨頭引領創新、公立機構夯實學術、中小型館差異化共生” 的健康格局,將取決於政策引導、行業自律與公衆選擇的共同作用。當然,科技巨頭的入場既是挑戰,也是推動中國美術館體系從“規模發展”轉向“質量與創新驅動”的重要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