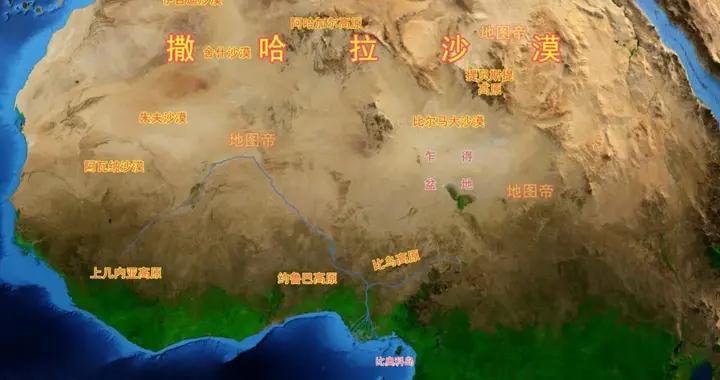白左當道,極右橫行,歐美政治環境爲何越來越極端
閱讀此文前,誠邀您點擊一下“關注”按鈕,方便以後持續爲您推送此類文章,同時也便於您進行討論與分享,您的支持是我們堅持創作的動力~

2010年,中文互聯網上誕生了一個新詞彙,“白左”,用以形容歐美那些癡迷於政治正確,無視現實問題的人。
當時,這一羣體佔據了歐美輿論的絕對主流,就連歐美政壇都充斥着濃烈的“白左”氣氛,大肆推行各種自損國家根基的難民庇護、無腦環保、LGBTQ+政策,看得外界目瞪口呆。
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些政策的惡果開始顯現,歐美的政治氛圍又迅速轉向極右,那些曾經被邊緣化的高喊着“本國優先”,全盤反對自由化、國際化的極右民粹政客迅速崛起,成爲了歐美政壇的新星。
這樣從白左無縫轉換到極右的變化,難民讓人感慨,歐美的政治環境,未免太過極端了,難道就不能選出個能平衡國際化和民族主義的正常政府嗎?

建制派落寞
其實,曾經的歐美政客,並不是今天這副非左即右的極端樣子。
相反,他們非常清楚,作爲國家的領導者,應該儘可能站在中間立場,以最大程度上彌合社會矛盾,集中力量推動國家發展。
回顧20世紀的歐美選舉,其實不難發現,當時各黨派之間的分歧並沒有今天這麼嚴重,甚至許多競選人在大多數選舉議題上所持的觀點高度相似。
並且,無論在選舉時,各路政客爭得多麼激烈,在選舉落幕之後,大家基本還都能維持最基本的和諧。
至少,當時的歐美議會反對派很少會爲了反對而反對,對於政府正當合理的政策主張,反對派議員也會投出支持票。
雖然這種投票的背後,往往是各種精英小圈子內部的利益勾兌,但不管怎麼說,當時的歐美至少在表面上實現了團結。

這些奉行精英內部協調,以推動政策進展持續的政客,今天被稱爲“建制派”。
曾經,這些建制派精英憑藉手頭的豐富資源,是歐美政治舞臺的絕對主流。
畢竟,歐美雖然名義上“自由民主”,各級領導人都要由選舉產生,任何公民只要符合參選條件,都可以競爭領導人職位。
但是實際上,想要在選舉中勝出,需要進行大量政治宣傳,讓選民瞭解候選人的政治觀點,進而爲其投票。
普通人既沒有時間、精力,長期脫產到各地搞宣傳,也沒有資源、渠道,讓傳統媒體爲他們打廣告,很難在選舉中戰勝有錢有閒有渠道的精英。
然而,進入21世紀之後,隨着互聯網的興起,傳統媒體對輿論的壟斷被撬開了一條縫隙,普通人獲得了廉價便捷的發聲方式。

此時,歐美的建制派政客們剛剛整了一堆反恐戰爭的爛活,又碰上了2008年金融大危機,民衆對政府的表現極爲不滿。
這種不滿在過去傳媒不那麼發達的時候,會被主流媒體過濾、隔離,等到經濟危機週期過去後被自然消化。
但這一次,這種不滿被迅速宣泄出來,進而發展爲對傳統建制派精英的質疑。
建制派爲了保住權力和地位,不得不接受“按鬧分配”的原理,與那些能夠引起社會聲浪,在傳統觀點裏偏向極端的勢力合流。
相比容易讓人聯想起法西斯的極右,擁有道德進步光環,又早已被資本主義異化,還能夠吸引大量民衆,尤其是不諳世事卻行動積極性高漲的年輕人支持的白左顯然更受建制派的歡迎。

可白左素來擅長按鬧分配,建制派卻要大局爲重,這造成的結果就是,明明建制派的根基更深,白左卻能獲得更重要的位置,實現更多自己的政治主張。
在外界看來,就是曾經屬於中間派的建制派立場也開始向白左偏移。
建制派對於這種變化心知肚明,卻毫無辦法,因爲他們必須用讓利換取白左的支持,才能繼續穩住自己的位置。

左右互搏
然而,白左這個羣體,在某種意義上和槓精高度類似,向來是只管提出問題、要求結果,至於具體應該怎麼做才能在不造成重大損失的前提下達成目標,這些人是毫無研究的。
這就導致,在民間當反對派的時候,白左確實能夠對社會起到正面作用:他們提出問題引發社會輿論聲浪,進而迫使政府重視、改進,推動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可一旦這些人掌權,按他們那高度脫離現實的邏輯行事,那對於國家來說就是一場災難了。
過度激進的環保政策,會給工業造成重大阻礙,尤其是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資本在歐美建廠被環保政策阻礙,導致成本激增,少有會繼續死磕到底的,多是會選擇換個國家投資。

這在白左眼中不是什麼問題,或許他們還會高興於這些不環保的產業搬走後,周邊的空氣變得更加清新了。
可對於國家來說,工業纔是國力的根基,去工業化意味着隨時可能受制於人。
好在歐美作爲工業先發國家,還有些家底能給他們禍害,又有輿論霸權作爲裱糊,這種衰退一時半會並不會被民衆注意到。
但去工業化造成的高薪且穩定的製造業崗位流失,卻是歐美民衆會切身體會到的。
在普通民衆在抱怨好工作變得難找時,白左不但不考慮如何擴大就業,反倒用各種“人權”政策,讓歐美民衆的處境雪上加霜。
雖然他們所推行的難民救助、多元平等政策看起來佔據了道德高地,可前者需要消耗大量物力財力,而這些錢財最終都要從普通人的稅收中來,後者則是強行將更多蛋糕分給LGBTQ+羣體。

久而久之,被白左政策傷害的普通人自然會對白左議題產生不滿,但在中間派,甚至是中右派都已經相當程度上與白左合流的情況下,他們在正當要求總是會被忽視。
在二戰後一直被政治主流排斥的極右翼勢力注意到了這一情況,敏銳地意識到,這將會成爲他們捲土重來的機會。
爲了獲取這些失落的普通人的支持,歐美極右翼也開始迎合主流,用傳統上屬於中間派甚至是偏左的表達,來包裝自己的主張,以淡化極端主義色彩。
得益於歐美白左推行的快樂教育,大多數歐美民衆對政治立場的認知主要依據政治術語,根本沒有意識到,在光鮮的包裝之下,極右翼的底色其實並未改變。
對社會現狀的不滿,讓他們在極右翼淡化了自身的法西斯色彩之後,將唯一會響應他們的焦慮,重視他們超過外來難民、性少數羣體的極右翼當成了最後的指望。

就這樣,最近這些年,歐美的極右翼實力迅速擴張。
在美國、意大利,極右翼的特朗普和梅洛尼先後贏得大選,已經成功掌握了國家權力。
在法國,極右翼也差點成爲議會第一大黨,哪怕後來中間派和左翼聯手狙擊,依舊獲得了143個席位,與中間派和左翼三足鼎立,分庭抗禮。
哪怕是在因爲二戰歷史影響,對極右翼防範最爲嚴格的德國,極右翼的選擇黨也在最近一次選舉中,以20.8%的得票率成爲議會第二大黨。
這些歐美主要國家尚且如此,更不必說那些體量更小,對難民危機、經濟危機抵抗力更差的小國。
而極右翼的回潮,又引發了傳統中間派和左翼的高度警惕,歐美社會的對抗氛圍日益激烈。

看到這樣的情況,難免有人疑惑,歐美社會就不能選出一個不信奉白左,也不搞種族主義的正常政客嗎?
遺憾的是,這個問題的答案確實是肯定的。
在歐美的選舉政治環境下,政客爲了贏得選舉,就必須設法吸引更多人的眼球,從傳播學的角度來講,無疑是越極端的主張,越能夠做到這一點。
更加糟糕的是,由於無論是白左還是極右,都是擅長破壞多過建設,憑藉極端主張上位的政客在執政之後,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歐美社會所面臨的問題,只會人情況進一步惡化。
而社會經濟狀況的惡化,又會導致普通民衆生活水平下降。

所謂窮則思變,當民衆的日子變得難過起來,出於對變革的渴望,他們的政治立場也會從中立轉向極端。
如此一來,白左和極右的聲勢便會進一步壯大,反倒是傳統上佔據社會主流的中間派會被不斷擠壓。
當中間派不再佔據主流地位,甚至其體量已經無法與左右翼中的任何一方單獨抗衡時,中間派就會成爲左右共同攻擊的對象。
歐美如果不能及時重塑社會共識,未來的左右互搏只會越來越嚴重,直到社會內爆爲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