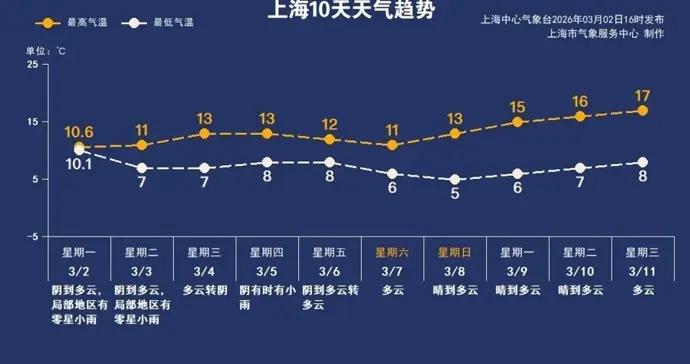《廬山戀》裏的野菊花 | 文匯筆會

去廬山採風,到達廬山風景區的當晚,知情者告訴我,山上有家電影院,叫“廬山戀影院”,電影院每天每夜滾動放映電影《廬山戀》,“可以隨時去看”。還說,這家電影院已經創下《廬山戀》單片放映場次最多的吉尼斯世界紀錄。
對這家電影院早有耳聞,並對這種看似決絕執拗的做法有一種心嚮往之的感佩和讚歎。到了酒店,放下行李,急匆匆喫了晚飯,便用手機導航,去了廬山戀影院。
天色向晚。去往電影院的路上,山路崎嶇,路燈暗淡,思緒不由回到了兒時星夜奔赴十幾裏山路去看電影的往事。
我的家鄉鐵卜加,坐落在青海湖西岸海拔3400多米的高寒草原上,是個只有十幾戶人家的小牧村。小牧村緊挨着一座古城遺址。關於這座古城,史書裏有明確記載,它叫伏俟城,是歷史上一個叫吐谷渾的部族修築的,是他們的都城,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歷史了。史書裏還標出了這座古城的位置——“青海西十五里”——這一記載,也讓我的家鄉鐵卜加小牧村有了一個明確的地理座標。那時,伏俟城是我和小夥伴們經常去玩兒的地方。高大厚重的城牆早已坍塌,與草原渾然一體,但依然能夠阻擋從東西南北刮來的風。進入城池,便能感受到相對於無邊荒野的暖和,也是因爲這個原因,城池內的野草肆意生長,一人多高的芨芨草密集林立,爲我們提供了捉迷藏玩兒的絕佳掩體,成了我們瘋玩兒的樂園。除了伏俟城,還有一處我們經常去玩兒的地方,我們叫它草原站,在“青海又十五里”——這當然不是史書裏的記載,而是我的杜撰。蹊蹺的是,青海湖距離伏俟城,也就是我的鐵卜加小牧村大約十五里的樣子,而草原站距離鐵卜加村,也大約有十五里。青海湖、伏俟城、草原站形成了三點一線。如果說,伏俟城遺址內外葳蕤的野草給了我們大自然荒野的體驗,那時的草原站,在我們眼裏則是一座大都市。那裏有馬路、商店、學校、醫院、郵局。夜晚來臨,一臺發電機張揚着嘯叫聲開始發電,供那裏的人家照明。那時的鐵卜加小牧村還點着油燈和蠟燭,出了屋門,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便吞沒了整個兒草原,而那時的草原站卻燈火通明,路邊的電燈和每家每戶映襯出窗外的燈光像一簇落地的星星,照亮了那裏的黑夜。
更讓我們着迷的是,那裏還有一座電影院,十天半月就會放映一場電影。於是,在有電影放映的夜晚,伴隨着夜色降臨,我和我的小夥伴兒們便丟下書包和作業本,從鐵卜加村向着草原站進發,我們風雨無阻,不論冬夏,迎着那裏漸次亮起的一片燈光,直奔電影院。後來我才知道,草原站全稱青海省鐵卜加草原改良試驗站,是省上設立在我的家鄉的一處科研機構,據說在從事牧草繁育改良、草地退化治理等工作,直屬省上主管。省上體恤在這片高寒草原工作的員工,放映電影,算是對他們寂寥單調的生活的一點撫慰,而這樣的福利,無意之間也惠及了我們。
我清楚地記得,電影《廬山戀》就是在草原站的電影院裏觀看的。那天晚上,電影院裏坐滿了人,我和小夥伴們沒有座位,就站在過道里。那是一個冬夜,我們從冷風嗖嗖的曠野徑直走進電影院,一股暖意即刻裹擁了我們,當銀幕上出現夏日的葳蕤和燦爛,我甚至感受到灼熱的陽光貫穿了我的全身。那時我十三四歲,正當少年,或許是在生理發育上還沒有開竅,現在回想起來,我對電影裏後來被稱爲“中國電影第一吻”的那場熱血沸騰的“吻戲”毫無印象——據一個當年和我一同去看電影的小夥伴後來說,當時,看到那場“吻戲”,他的臉燒哄哄的,“可能都成猴子屁股啦”。他說,電影院裏還響起了幾聲騷動不安的噓聲——我並不記得這些,卻深深地記住了出現在電影裏的一束野花:男女主人公並肩行走在一條綠意盈盈的山路上,在山路拐彎的地方,男主人公發現腳下的草叢裏盛開着一束金黃色的野花,便停步躬身,摘了野花,即刻送給了女主人公,女主人公欣喜地接過那束野花,雙手捧在了胸前。之後的電影畫面裏,女主人公一直手捧這束野花,從陽光燦爛的白天到暮色凝重的黃昏,野花伴隨着他們走過鬆濤、竹海,山泉、石林。直至晚風送來夜色,男主人公把女主人公送到了酒店門口,他們依依不捨地揮手道別(下圖爲《廬山戀》劇照)。再後來,這束野花便出現在了女主人公入住的酒店房間,它被插在一隻小小的敞口花瓶裏,裝點在梳妝檯上,擺放在窗戶邊上。這束野花最後出現在銀幕上,是在一個風雨交加的黑夜,刺耳的雷鳴聲裏,短促的閃電照亮黑夜的瞬間,那束野花在窗臺上展露出耀眼的金黃,幾片花瓣悽慘地飄落在桌面上。女主人公得知她的身份(華僑)和行爲連累了正在接受審查的男主人公,滿懷羞愧與不安,還有悲憤與不捨,與男主人公不辭而別,從此他們各自天涯……看到這組畫面,我這個尚未開竅的少年卻似乎感受到了什麼,心中泛起隱約的悲傷,一種流質的液體在心裏湧動着,差一點兒從眼睛裏冒出來。
這束野花是什麼花兒呢?在我心裏比那場“吻戲”還重要的這一束野花,電影裏卻隻字未提它的名字,便把這樣一個疑惑留給了我。寒來暑往,那年暑假結束,開學的第一天,我的一個小學同學把一本《廬山戀》的小人書帶到了學校來,小人書的畫面是電影《廬山戀》的一幀幀截圖。“截圖”是時下的技術和說法,不知道那時候是怎麼做到的,是對電影畫面的翻拍?還是在電影拍攝現場專門安排了一位攝影師?不得而知。爲了能看那本小人書,確切地說,爲了弄清楚電影裏那束野花的名字,我以幫那位同學寫語文作業作爲交換條件,從同學那裏借來《廬山戀》小人書,並在課間休息的十分鐘裏看完了小人書。小人書裏還真提到了那束野花,但只給了一個模糊的名字:一束野菊花。
其實,野菊花這個答案我是之前就猜到了的——從電影畫面去看,那束野花很像是我家鄉鐵卜加草原常見的野生菊科植物高山紫菀——這個學名是我後來才學會的,那時候我們叫它“魯目梅朵”——羊眼睛花(下圖)。

那時候,就覺得這個名字生動又貼切:自小就是牧童,每天放牧在草原上,早出晚歸,總是與羊羣零距離接觸,熟悉它們的眼睛,甚至能讀懂它們的眼神。清晨,初升的太陽剛剛照在羊圈向陽的牆面上,在羊圈裏圈了一夜的羊們便陸續站起來,眼睛齊刷刷盯着羊圈門口,急切等待着主人把它們放出羊圈,趕到草原上去啃食牧草。它們的眼睛微微凸起着,在頭部的頂端兩側錯落有致地閃爍着,放眼望去,形成了亮晶晶的一片。每每看到這個情景,我即刻就會想起在夏日草原上一片片開放着的高山紫菀“羊眼睛花”。高山紫菀也是擠擠挨挨地簇擁在一起,隨風擺動着,錯落有致地閃爍着。仔細去看,花朵中心微微凸起的暗黃色花蕊就像是羊眼睛深色的瞳孔,圍攏着花蕊放射狀伸開的舌狀花瓣,形成了一個傘房狀花冠,看上去就像是從瞳孔擴展到虹膜的均勻細微的纖維組織。每每看到這樣的情景,我心裏就會掠過一縷驚喜和詫異,就想,我們的先祖把高山紫菀稱作“魯目梅朵”——羊眼睛花,這是多麼形象啊,這一定是在千百年來的生活經驗裏屢屢觀察和比對後的發現和確信呢。這樣的發現和確信,來自對大自然和遊牧生活的稔熟和熱愛,來自被風雨一遍遍洗滌過的內心的純淨吧。
在我的家鄉,除了高山紫菀,還有一種野菊花,名叫狗娃花——後來發現這個名字居然是它的學名。巧合的是,我們那時候就叫他“齊目梅朵”,意思是“狗眼睛花”。狗娃花乍看上去很像高山紫菀,只是略微要比高山紫菀小一些,就像是狗眼睛比羊眼睛小一些一樣。狗娃花也不像高山紫菀那樣成片成片地開放,而是經常三五朵一簇地出現在山路的路畔,羊圈的一角,就像是家裏的狗兒,總是喜歡躲在爲人所不注意的角落。
但可以確信的是,電影《廬山戀》裏出現的那束野菊花(上圖),不是我家鄉的高山紫菀,也不是狗娃花。因爲這兩種野菊花,頂狀花序的花冠都是明麗的淡紫色,而電影裏的野菊花是金黃色的。如果說,盛開在家鄉鐵卜加的野生花卉裏,最像《廬山戀》裏的那束野花的,則是另一種野花,我們叫它“崗嘎梅朵”。這種野花並不常見,明麗的金黃色舌狀花瓣圍着略顯暗淡的黃褐色花蕊,不事張揚地盛開在荒涼的山畔或流石灘上,收斂和遮掩着自己的美麗,儘量不讓人們看到它。它不但好看,還散發着淡淡的清香。小時候,我們在草原上放牧,抑或去撿拾蘑菇,每每在山野遇見,就會採摘一些未被牛羊踩踏,花朵尚未盛開的枝葉,帶回家裏,晾乾,與柏香枝、火絨草等混合在一起,做成一種用來煨桑的材料。每逢節日,或者藏曆初一十五,家裏的大人起了牀,洗漱一番,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到自家門口的煨桑臺煨桑。所謂煨桑,就是把這些煨桑用的材料放在煨桑臺上點燃。這些天然具備濃郁香氣的植物枝葉,一經火燒火燎,香氣就被激發出來,一時間,伴隨着嫋嫋青煙,滿天滿地瀰漫着植物的異香,人們不由得要深深吸一口氣,讓這樣的香氣肆意浸染自己的身心。小時候,曾經問父親爲什麼要煨桑,父親回答說是爲了讓住在天上的神靈們高興。“他們可以不喫飯,聞到好聞的味道就能填飽肚子。肚子飽了,他們就很高興,就會給人們帶來風調雨順,平安康樂。”父親說。聽了父親的話,我抬頭看着頭頂空曠無垠的藍天,想象着那些看不見的神靈拿着碗筷,大快朵頤地喫着桑煙幻化成的各種美味,滿懷歡喜,就把風調雨順和平安康樂撒向了人間大地。後來長大了,知道煨桑是一種盛行在青藏高原上的民間煙供儀式,不單單是爲了愉悅神靈,通過點燃植物枝葉產生的煙霧,也能起到抑菌滅菌,淨化環境的作用——藏語“桑”的意思原本就是清潔、淨化的意思。
後來從書本里知道,“崗嘎梅朵”的學名叫矮垂頭菊,是一種生長在海拔3000米以上高寒地帶的高寒植物。廬山地處亞熱帶季風氣候區,這裏的野菊花,指定不是高原上的矮垂頭菊。矮垂頭菊除了被用作煨桑材料,在藏醫藏藥中也用於清熱解毒,預防腫脹等——少年時代,每每看到父親虔誠地煨桑,點燃起包含有矮垂頭菊的煨桑材料,就想,父親總是勤勉地煨桑,供奉天上那些看不見的神仙,也不知道送達了沒有。而《廬山戀》裏的男主人公,則直接把水靈靈新鮮的野菊花,捧送給了天上仙女一樣的女主人公,即刻贏得女主人公燦爛的笑容。
再後來,到縣城上了中學,有一次聽語文老師講古代漢語詩歌,就講到了陶淵明,說他出生在廬山腳下,看着山頂閒散的流雲,流雲間閃現又消隱的日出月落,日出月落裏枯榮往復的四季變換,長大成人,後來在外爲官,被山野的清風激盪撫慰過的心身渴望自由清淨,承受不了紛繁世俗的束縛和羈絆,便辭官回家,復又回到兒時的村寨,避世歸隱。歲月清淨,時日淺淡,“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便是他隨性自然的生活寫照。還說陶淵明愛菊寫菊,以菊花的清雅高潔自比,修心修身。“他採摘的野菊花,叫廬山野菊。”語文老師說。聽老師如此說,我的思緒瞬即便鏈接到了電影《廬山戀》——男主人公送給女主人公的那束野菊花,難道就是1600多年前陶淵明採摘的那束野菊花嗎?而《廬山戀》裏的野菊花,不再有那麼多的寓意或象徵,只是簡單直接地表達着愛情的熱烈和驚喜。
那晚在“廬山戀”看《廬山戀》,當銀幕上出現那束野菊的特寫鏡頭,我急忙拿出手機,對着銀幕翻拍了一張圖片。回到酒店,我把圖片導入豆包,豆包經過一番辨識,用溫柔女性的聲音告訴我,圖片上的花卉是一束塑料或布藝材質製作的仿真花。不知道豆包說得對與否,我心卻還是忽然沉了一下。從少年時代,就像一個謎一樣藏在心裏的那一束野菊花,難道僅僅是一個微不足道的道具?不會是這樣一個無厘頭的結局吧。
此行在廬山採風,向人討教,知道廬山上還真有一種菊科植物叫廬山野菊,說它是野菊在廬山地區的生態型變種,相對於其它地方的野菊,其葉子背面的毛被物較多,植株也略微大一些。行走在廬山崎嶇的山道,期望着能像詩人陶淵明,抑或是電影《廬山戀》裏的男女主人公一樣,邂逅一束野菊花,不採,只想近距離看看。或許是已經錯過了野菊花的花季,未能如願,或者說,留下了一個在對的季節,再去廬山觀花的藉口吧。
據有關新聞報道,廬山在野生植物保護方面採取本底調查、就地保護、野外迴歸、遷地繁育以及種質庫建設等一系列措施,使廬山上的原生植物得到了很好的保護,不知道這些植物裏有沒有廬山野菊,如果有,但願它也能有這樣的厚待。
作者丨龍仁青
編輯丨蘆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