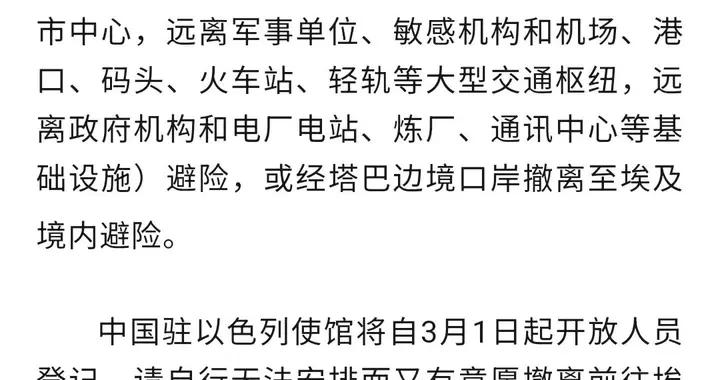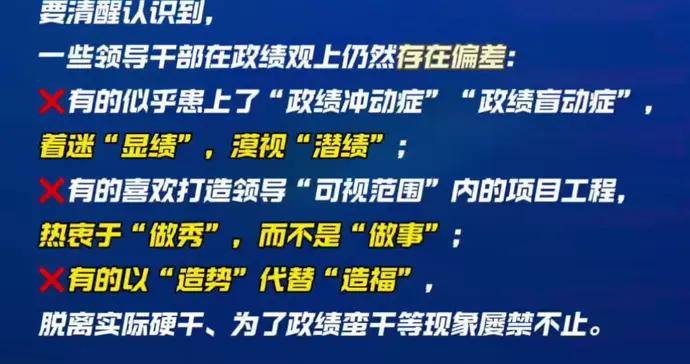這部 9.1 分的神劇,我有些不同看法



在經典文學敘事中,家庭的裂痕通常被描繪爲一種慢性的“自身免疫病”。 沒有洶洶的來勢和激烈的震盪,而是在亨利·詹姆斯的客廳裏悄然滋生,在威廉·福克納的南方莊園裏默默發酵。它的痛感,源於時間的延綿,源於我們在閱讀過程中與人物共同煎熬,去感受那種無處可逃的窒息,去承受道德倫理漫長的拷問。
對時間的敬畏,曾經也是熒幕敘事的基石。它凝聚在英格瑪·伯格曼冷峻到殘酷的特寫鏡頭裏,用無聲的對峙丈量情感的崩塌;它潛伏在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幽靈一般的陰影下,用危機降臨前被無限拉伸的延宕製造令人焦灼的恐怖。這些創作者篤信,真正的破碎往往發生在靜默時刻,真正的驚心動魄往往並沒有大喊大叫。
然而,不知從何時起,我們似乎很難再沉下心去閱讀一部深沉厚重的家庭小說,或是耐心地觀看一部節奏緩慢的情感悲劇。從這兩年熱播的歐美家庭倫理劇中,我們能看到畫風的明顯轉變。似乎是爲了在這個注意力被算法切碎、被倍速消磨的時代留住觀衆,創作者們不約而同地拋棄了對親密關係解剖式的審視,轉向了對愛恨糾葛迷宮式的探險。於是,反轉的密度置換了敘事的厚度,解謎的快感取代了共情的質感。如今的熒幕家庭故事越來越像是一場爭分奪秒的障礙賽,鏡頭無時無刻不在製造驚奇,生怕慢了一秒,屏幕前的你我就會滑走離場。

這在前不久引發熱議的《都是她的錯》中體現得淋漓盡致。不得不承認,這部改編自愛爾蘭作家安德莉亞·瑪拉同名暢銷書的家庭懸疑劇極其“抓人”,它深諳當代觀衆的心理節拍,尤爲了解如何捕獲大衆的焦慮。驚悚的開篇堪稱教科書級別:一個平平無奇的下午,陽光很好,社區很安全,去接兒子回家的女主角瑪麗莎按響門鈴後,開門的卻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人。那一刻,沒有怪物跳出來,卻讓人後背發涼,因爲最深的恐懼往往並不來自黑暗的未知,而來自人們最信賴的確定性的突然失靈。更不用說,在經典敘事法則中,孩子的消失通常被認爲是現實秩序瓦解的元點,意味着世界在本體論意義上的坍塌。劇集大可以在這份“失靈”中紮根,去細細描摹一位母親在孩子失蹤後、面對巨大空洞時的精神狀態,畢竟飾演女主的是薩拉·斯努克,這個剛從《繼承之戰》走出、頭頂無數光環的劇後級演員,完全具備承載這份重量的能力,尤其是她那雙幽深、總是含着淚水的眼睛,幾乎就是爲了凝視深淵而存在的。
但是,流量時代不相信喪失的虛無,算法邏輯容不得深淵前的駐足。幾乎就在危機發生的瞬間,觀衆被立即告知:這不是一起簡單的走失,而是一個巨大的局。接下來,劇情迅速開啓了一種“狼人殺”式的智力遊戲,故事不僅講得快,而且講得“狠”。每隔十幾分鍾,人物關係就會發生一次劇烈的重組;每一集結束前,都會留下一個顛覆預期、戛然而止的懸念,讓人慾罷不能地點擊“播放下一集”。在這個不斷追逐、又不斷轉向的過程中,我們不再關心瑪麗莎“感受”了什麼,只關心她“發現”了什麼。

用驚奇取代共情,並非《都是她的錯》的獨創。2024年網飛出品的《模範愛侶》可謂這種熒幕形態的極致。妮可·基德曼坐鎮的頂配班底使它自帶高貴氣質,鏡頭俯瞰風光旖旎的海濱豪宅,掃過衣香鬢影的華麗派對,柔和的光線散發出一股濃濃的“靜奢風”。然而,優雅的視覺質感無法掩蓋其乾癟的劇情內核,開場的集體羣舞和近乎戲謔的“全員嫌疑人”設定,將本該莊重的謀殺案消解爲了一場浮華的富人喧囂。泛娛樂化的輕盈感彷彿是創作者在對觀衆拼命眨眼:“別當真,這就是一場上流社會的遊戲。”那些令人大跌眼鏡的反轉不是爲了揭露人性的幽暗,而是爲了讓觀衆震碎三觀,沉浸在一種“有錢卻痛苦”的虛假撫慰中。
當“不讓觀衆猜到結局”成爲創作的至高指令,故事的連貫性和人物的邏輯自洽性便成了犧牲品。這在另一部熱映劇《無罪的罪人》中表現得尤爲露骨。爲了讓看過斯考特·杜羅原著的觀衆依然感到“震驚”,創作者不惜在最後關頭更改兇手設定,讓飾演男主的影帝傑克·吉倫哈爾原本充滿爆發力的表演最終落腳於一個令人錯愕的結局。爲了使觀衆在最後一秒鐘也能倒吸一口涼氣,這個爲了反轉而反轉的改編徹底背叛了人物行爲的內在邏輯,吞沒了整個故事原本對於心理黑洞和司法困境的深度檢視。

當然,這並不是說反轉是一種原罪,恰恰相反,它一直是戲劇的核心要素。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曾指出,悲劇最震撼人心、也最有力量的時刻是“突轉”與“發現”的同時到來。比如,當俄狄浦斯王得知那個被他殺死的長者正是自己的父親時,“突轉”意味着人物從無知轉向有知,“發現”帶來的是一種痛徹心扉的覺醒和對命運必然性的臣服。但遺憾的是,在當下盛行的“快消”類型劇中,只有令人震驚的“突轉”,卻鮮有令人頓悟的“發現”,那種需要漫長鋪墊才能達到的敘事高潮早已被幹脆利落、即時高頻的敘事多巴胺所取代。
《都是她的錯》也未能免俗,甚至又提高了一個段位。當劇集走到後半程,觀衆赫然發現,所有的混亂竟源於一場“嬰兒調包”。而後,隨着多年來縱橫交錯的謊言被一一拆穿,一切的始作俑者終於浮出水面。在這裏,古希臘式的命運錯位被處理得充滿了人爲的算計,所有機緣巧合也被安排得嚴絲合縫,本該具有悲劇意味的“突轉”異化成了一種純粹的奇觀。當真相大白,我們感受到了邏輯閉環帶來的快感,全然忘記去體會命運捉弄時的無助感,去品味生命陡然實重時的無力與無奈。
當人物變成了搭建情節的積木,這部劇最值得深思的矛盾點也因過度簡化而流於表面。劇名“都是她的錯”本身是一個極具社會學意義的諷刺,直指文化潛意識中根深蒂固的“母職懲罰”——一旦孩子出事,母親總是第一個被審判的“罪人”。瑪麗莎那種時刻處於崩潰邊緣的自責,本該是這部劇最深刻的底色,它是對女性道德完美主義枷鎖的一次生動詮釋。但爲了配合懸疑劇的爽感邏輯,劇集放棄了在灰度地帶的深挖剖析,轉向追求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它不僅塑造了一個哥特式的惡棍丈夫,一個集精神操控、冷血謀殺、縝密欺詐於一身的“完美”反派,更讓本應是女性覺醒的高光時刻淪爲一場“受害者”變“加害者”的復仇反殺。從戲劇效果上看,瑪麗莎用大豆過敏“偷殺”丈夫的結局無疑是精彩而痛快的,因爲它精準擊中了觀衆渴望“清算”的情緒爽點。但本質上,這種處理方式又是格外偷懶的。它將妻子的痛苦簡單歸因於嫁了一個惡魔,而只要殺死了惡魔,世界便清朗了;它完成了“都是他的錯”的反轉、將高潮定格於“惡有惡報”的圓滿,實際上了迴避了那種平庸、瑣碎、看似正常卻令人窒息的婚姻困境,模糊了更爲普遍、也更爲隱蔽的權力結構與道德綁架。

不可否認,這類“快消”類型劇的確“熱銷”,總能輕輕鬆鬆登上熱播榜、火爆社交平臺。我也必須坦白,《都是她的錯》曾讓我追劇追到停不下來。這不僅歸功於它們精良的製作和頂級演員的加持,更因爲它們在這個充滿了不確定性與不安全感的時代,牢牢抓住了人們內心深處對於秩序的嚮往。它們製造巨大的混亂,但承諾徹底的重建;它們展示超出認知的陰謀,但保證所有謎團最終會有一個確定的答案。對身處難以釐清的現實世界、不斷遭遇邏輯失效的大衆而言,它們提供的“可控的失控感”,無疑是一種有效的心理代償。
但我們同樣應當意識到,當我們越來越將這類劇集當作一種情緒宣泄的出口、一種社交媒體的談資時,我們正在不自覺地參與一場關於審美的重塑。在“敘事加速”的裹挾下,複雜曖昧的故事正在被簡單化爲拼圖遊戲,人性灰度的凝視正在讓位於通關打怪帶來的爽感刺激,而那些關乎生命本質、需要在靜默與沉思中才能生長出來的領悟,正在被視爲拖慢節奏的累贅而遭到無情摒棄。技術給了我們跳過片頭、倍速播放的權力,卻也似乎剝奪了我們忍受未知的耐力。當我們不再願意在一個沒有反轉、沒有絕殺、甚至沒有結局的故事裏駐足,我們失去的其實是理解真實世界的能力,因爲那裏往往沒有驚奇、沒有天衣無縫的巧合,沒有能被一招斃命的惡魔,只有面對斷裂時的手足無措,深陷困頓中的拼死掙扎。
很多時候,慢一點,才能看得更清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