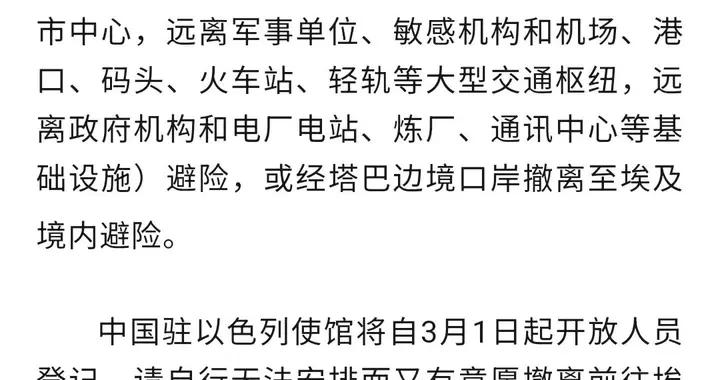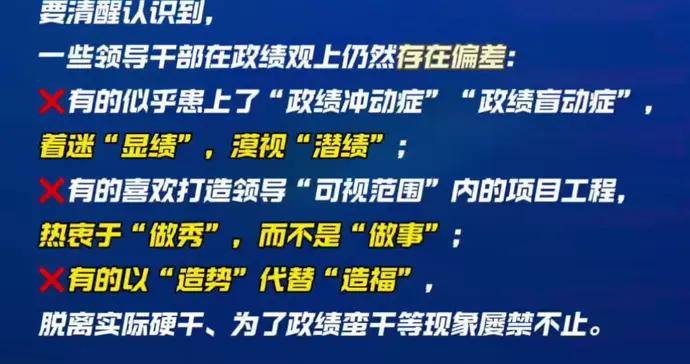家宴什錦菜——亂書房食單之一丨文匯筆會

日本電影《小森林 冬春篇》(2015)劇照
在北京喫了幾次素菜館,有一家還是有名的連鎖店,幾次邀約,不想再去。朋友詫異,且不解,以爲從不忌口、而且也從不問菜系、遇美食而一概接納的“老牌食貨”,獨獨拒絕素食?這真是誤解。在我的覓食生涯中,素食是不缺席的。但我遇食看重的還是真味,而對過於擺場的花哨食事總會婉卻。素食看重一個“素”字,一旦“素”成了“繁”,那就離題了。這家素食店是過於講究外在的形式,而被我冷淡的,我不拒絕傳統的素食。
反之,我對素食總懷好感,這種好感也與母親有關。母親信佛,每月初一十五,必焚香齋戒,行素食。每月到了母親的齋戒日,我們全家都會與母親一道喫素。這是我們的家風,也是對母親的尊重。在平時,受限於時局和條件,本來就少於葷腥,因之對素食並不陌生。空心菜,地瓜幹,曾陪伴我們度過艱難的歲月。素食有素食的特殊滋味,是平日飲食中的偶然,也是難得一遇。
那年山西友人邀謁五臺山,特許與僧衆長老一道敬了齋飯。佛偈,經咒,鐘磬,肅穆,一菜一飯,條席而坐,飯可再添,不限量,餐後有限量水果。這次素餐,可感可念,一記於今。於是聯想起早年遊南京雞鳴寺,那一碗素面也留下美好的記憶:記得是清湯麪,香菌,清油數點,青葉幾片,其味絕佳。於是養成習慣,到了寺廟,除了禮佛,便求一碗素面。在南嶽衡山,在舟山寺廟,在峨眉金頂,我像虔誠的信徒,求一路素餐,證一路喜樂。
這就尋到了我的家鄉,著名的廈門南普陀,這裏有佛學院,是南中國的佛家聖地,“此地古稱佛國,滿街都是聖人”,也是弘一法師早年修行護法的寶地,魯迅先生在廈大講學,經常在南普陀後山巖下讀書和思考。南普陀素餐很有名,每次到訪,我總謀求一享口福。在南普陀進素餐,總伴隨着一段美食佳話。據說當年詩人郭沫若受邀在此進餐,上來一道湯菜,清可見底,漂浮着一片半圓的豆製品。衆人求命名,詩人脫口而出曰:半月沉江!衆大喜。後來去過幾次廈門,也曾幾次拜謁南普陀,總是行色匆匆,與這道名菜失之交臂。生恐日後悔疚,也總求在廈門大學一條街上進一素食,算是完願。
詩人的“半月沉江”使我悟到:一道普通的菜餚,因有了詩意的融入,不僅可深化其中的美味,而且賦予了久遠綿傳的詩意。回到開篇言說,素餐可以如詩,但不宜隨意誇飾,誇飾則有違佛門清淨。再說母親的素餐,她是做素餐的能手,極品是舊曆正月初一的那場素食宴。閩俗舊曆年的除夕宴,不論貧富、尊卑,一律都是大魚大肉上席,葷腥的腸胃需要調節,素食於是順勢登場。這就說到我的母親,當家人都沉浸在祝慶春節歡樂時,母親默默地完成了她的“壯舉”:全素十樣菜,適時上桌!這是豐盛的除夕宴之後的同樣豐盛的元日宴。
逢年過節,母親不僅是辛勤的勞作者,而且更是精明的領導者,她默默操作。母親是萬能的魔術師,轉瞬間,她變戲法似的端出了圓圓滿滿的十樣菜。全素,不重樣,花團錦簇,五彩競豔:帶着紅根的菠菜,清炒,用少量的鹽,紅綠相間,清爽明亮;紅菇燴木耳,紅色和黑色互搭,用生抽和淡淡的鹽和紅糖佐之;黃花菜炒山東粉,金黃色配白色粉絲,不用醬油,熠熠生輝;水芹菜炒豆腐絲,水靈靈又脆生生,拌以香油,等等。其餘,花菜,包菜,芋頭,慈姑,紅蘿蔔,白蘿蔔,膠東大白菜,都是母親手邊的素材。母親鎮定從容,運籌帷幄,視覺,嗅覺,或煎、或炒、或生拌,猛油,溫油,鹽、糖、醋、姜、味素,量大,量小,何者爲主,何者爲輔,全在她的掌控之中!
盛大的全素宴是供奉神明和祖先的。鞭炮、香燭,禮拜,一敬天地,再敬祖先,家人互敬,禮拜之後,家人方能分享這全素席。福州民間全素宴是母親從她的孃家閩侯鳳崗裏帶來的習俗,數代的遺傳,一至於今。近讀《文匯報》餘斌《南京過年“十樣菜”》(2025年2月5日“筆會”刊發),命題似乎相近,我家的全素宴或許是來自金陵的遺風?母親已去,家庭的什錦全素宴亦已失傳,這一席天下最美食也縹緲不可尋了!母親,家鄉,春節,元日,我對素食的懷念總是深深。
來源丨文匯筆會作者丨謝冕
編輯丨吳澤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