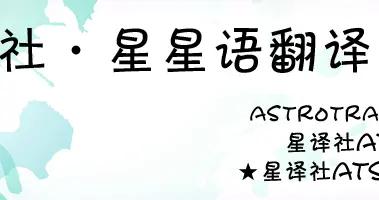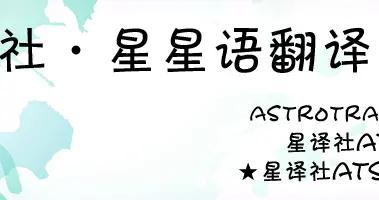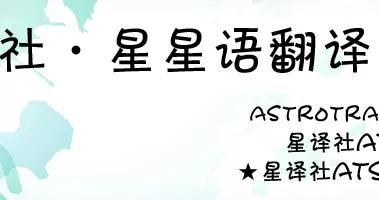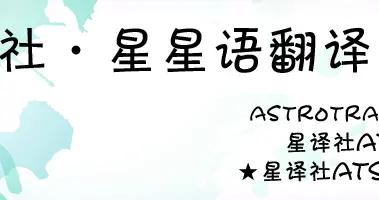(原則)魯哈伊爾:占星發展史
戴恩·魯哈伊爾(1895年3月23日-1985年9月13日),美國作家、現代主義作曲家、畫家、人本主義佔星家,現代占星先驅。
轉載請註明星譯社及譯者幻覺
本文節選自魯哈伊爾另一版《十二宮》文獻的前言部分,這一版於1972年發行,前言部分將根據具體內容分章節發佈。
魯哈伊爾:占星發展史
大多數占星師認同這個占星概念:占星是地球視角的天體位置與人類意識的具體事件、心理、集體、社會變化之間可建立的關聯性。天體運動,除了極少數的例外,都是週期可測性的。我們完全可以看到宇宙是個有秩序的整體,儘管這秩序還看不出那麼具體,畢竟我們紮根在大地生活,捲入地面活動並因此產生情感反應,而無法感受到宇宙的宏大圖景。但在我們思考那些相距甚遠的天體活動時,卻可以感受到天體在天空背景中勾勒出的莊嚴韻律:太陽、月亮、星辰的升落,新月和滿月,行星的合相以及其他週期性現象。因此,占星通過將人類在世俗環境中看似不可預測和偶然的經歷,與天體位置及其相互關係的週期可測變化聯繫起來,提供了一種極有價值的秩序感,這種秩序感進而給了人類一種超驗性質的安全感。
人類可以多角度呼應和解讀這個認識:地球周圍發生的宇宙動態與人類生活的內外變化之間,可以建立明確且相對可靠的關聯。顯然,這種呼應和解讀的具體狀況,從根本上取決於人類所處的進化階段,具體表現爲感官感知天空動態的能力、意識能力、心靈機能、智力、測量和解讀的物理、文化工具的發展。這一切體現在社會、宗教和文化環境中,也是這些環境爲觀星者提供特定的語言、基本信念和社會生活方式。
將佔星本身與占星師所處的社會文化條件割裂是毫無意義的,任何系統性的概念都必須根據行動、感知、思考生活所在的條件——包括個人、社會、地理環境——來理解。行動或思想的“真相”,或更確切地說,行動或思想的有效性,只能通過關聯到更宏大的社會、文化背景,甚至更深層關聯到人類(至少是部分人類羣體)進化的特定階段纔可以確定。
因爲這一點常被忽視,或被扭曲——以當下人類意識狀態去投射古人和其他種族的思想與情感——才導致了今日的諸多困惑。占星尤其容易成爲困惑滋生、教條蔓延的溫牀,無論這些困惑、教條是以所謂的科學分析、神祕學文獻出現,還是以靈性直覺或通靈信息的形式呈現。很多複雜理論和令人費解的解讀之所以存在,是因爲占星一直被視爲割裂於時代文化的孤立的東西,認爲占星就是使用着古迦勒底時期以來從未改變、還據稱現在仍然有效的神祕術語的“神祕學”。但這種術語顯然未能充分考量過去的漫長世紀中,人類意識、人對自己和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已經在認知上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所以當下對占星的興趣浪潮正遭遇各種障礙,還以含混的方式流入各種渠道。很多時候,這意味着失去了占星的基本功能:即爲人類帶來秩序感、和諧感和生活的節奏感——並且非常重要的是:占星服務的對象不是古埃及或古中國的古人,而是具有當代情感、精神和社會問題的現代人。
上古時代的地域中心占星
公元前六世紀“上古時代”結束——當時佛陀在印度生活和傳教,畢達哥拉斯活躍於希臘世界——在此之前,“上古時代”的人類意識(可能除了極少數例外)根本上是以地域爲中心的,是一小羣一小羣的人類羣體,他們的生活、感受和思考都圍繞着我們稱之爲“部落”的價值觀。
當時的部落羣體是人類整體的基本構成,部落對賴以生存的那一片大地的依賴就像胚胎對子宮的依賴,部落生活是整體的有機生活,每個成員都是完全融入有機整體的細胞,部落中的每個人都在精神上受羣體生活方式、文化、信仰和象徵的支配,不能違抗部落禁忌。人類在這個進化階段,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個體”,而構成各種羣體文化、信仰基礎的所有價值觀,都是特定地理、氣候條件下特定人種的表達。部落會面向過去尋找共同的祖先,或帶來過啓發性知識和精神凝聚力的神聖君主(即便不是事實上的君主),將其視爲羣體象徵。
在人類進化的這個階段,占星也以地域爲中心,並非以地球爲視角(即後來纔有的地心說)。每個部落村莊都有個中心點,這個位置被視爲世界中心,或通往世界中心的祕密道路的入口。我們今天所說的地平線,則是當時生活的邊界。地平線之上的天是偉大創造之神的居所,地平線以下的黑暗區域是神祕的冥界,太陽每晚退到那裏以重新積蓄力量,再次爲人類生活的那一塊平面世界帶來光明。當然,極少數祭司或通靈者可能意識到了地球是圍繞太陽公轉的球體,但即便上古時代存在過這類只作爲啓蒙儀式的、口口相傳的祕密傳統,它顯然也沒影響到當時的占星。
對於原始的部落人,占星是原始宗教象徵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預測週期性自然事件的手段,這些事件影響着羣體生活,特別是農業活動、牲畜交配,當時的生活條件下,人類意識聚焦於土地和整體有機體部落的整體福祉,占星也非常簡單,基本上只是所有天體——“恆星”、“日月雙光”——的升起、到達頭頂的中天位置和落下。
人們很容易區分出兩類星星,大部分星星升起和落下時彼此的相對位置保持不變,也就是說,這些光點在天空中運轉時形成的圖案是“固定的”。相對而言,還有些天體則各自獨立移動,有時甚至看起來逆行,它們被稱爲“漫遊者”,即行星(planet)一詞的原始含義,而經過訓練的觀星者可以看到,有些行星是小圓盤,不是一個光點,因此認爲,行星和恆星是截然不同的天體,人們注意到行星會週期性相合,並繪製它們的運動軌跡,以便進行測量並預測合相的發生。
以什麼爲背景來繪製? 顯而易見的背景或說參照系,是恆星構成的看似永久的圖案。但到這裏,我們必須認識到,在上古時代的人類看來,恆星不是固定的,他們看到恆星也會升起和落下,唯一真正固定的是目力所及的“地平線”,但在亞熱帶和沙漠夜空的清晰的黑暗背景上,恆星構成的整體幾何圖案看似“永恆”不變。所以只要將這些圖案細分,方便測量,就可以作爲參照系了。
爲理解星座的概念如何產生,以及它的象徵形式,我們只需認識到,所有部落都使用圖騰。這些圖騰與部落的氏族相關,這些氏族,在某種意義上代表着部落這個整體有機體內的功能器官。圖騰通常是動物,氏族成員認爲自己與這些動物有着特別的聯繫。當然,圖騰也可以是植物等任何在自然中可以觀察到的物體。
上古時代的人類試圖爲部落賦予更明確的形態和持久性,努力根據功能性的有機秩序的原則塑造部落。他們感知到宇宙是個有機整體,由兩種極化的宇宙生命力驅動。這種力量在占星中由日月雙光象徵,在古中國哲學中則由蘊藏在萬有的陰陽象徵,天與地在理想上被視爲兩種對立的極性:天是創造性的、神聖的,地是接受性的、豐饒的,但地上充滿需要被整合和馴化的野蠻能量——“馴化”(domesticated)的詞源domus,意思是“家”。
智者——古中國大約稱爲“天仙”——立於兩極之間兼具天地屬性,他們的任務是將天的創造秩序刻印在大地的自然中,並根據天的韻律和原理來組織部落生活。某些情況下,也存在相反過程:人類將部落圖騰投上天空,強調氏族感受到的、與特定天體間的緊密聯繫,這時的星座便以各種部落的圖騰命名,後來還有過“天人”的象徵,以人的器官對應星座。這種認知方式曾經在希臘盛行,那裏的英雄在死後被投向天空,星座以他們的名字命名。後來在中世紀歐洲,鍊金術和神祕學羣體將天空稱爲“天然自然”(Natura naturans),將大地自然稱爲“造化自然”(Natura naturata)——即象徵創造與接受的兩個極性。
古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等地區,季節因素不像歐洲北部那麼明顯,但尼羅河氾濫標誌着年度週期最關鍵的時刻,那片區域的占星師也是觀星者,現在可以肯定的是,他們的黃道是參考天空的星座設定的。我要再次強調,那時的占星以地域爲中心,不是以地球爲中心。那時沒有任何占星師會關注北極或南半球。涉及這部分的煩人問題,直到人類知道了地球是個球,和所有行星一起圍繞太陽公轉這個事實,纔開始出現——即西方人開始旅行並看到與歐洲截然不同的天空時。
到人類進化的這個階段,上古的占星就算沒有完全過時,至少也充斥着陳舊概念和古老認知,許多情況下已經不再具有任何實際意義。可同時,許多長期觀測和記錄的天象與地球事件之間的關聯性仍然有效,而這種有效性被帶入人類已經進化出的全新現實。以日心體系思考並可以全球旅行的人,在意識上已經很大程度地擺脫了對特定地理位置的強制依賴,社會也不再是地方性的或部落式的運作,人類已經從部落中解放出來,也是被連根拔起,人類開始了“個性化”。就算那時的一些人事實上仍然受到地域限制,但理論上,以及通過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普世宗教的新視角,他們都將自己視爲“個體”了,也已經被人類整體視爲“個人”。
如果占星無法考慮這些歷史、精神、智力和社會文化事實,導致對基本的現實條件視而不見,那麼使用過時術語和概念導致的占星理論混亂將始終持續下去,占星將始終得不到理解。